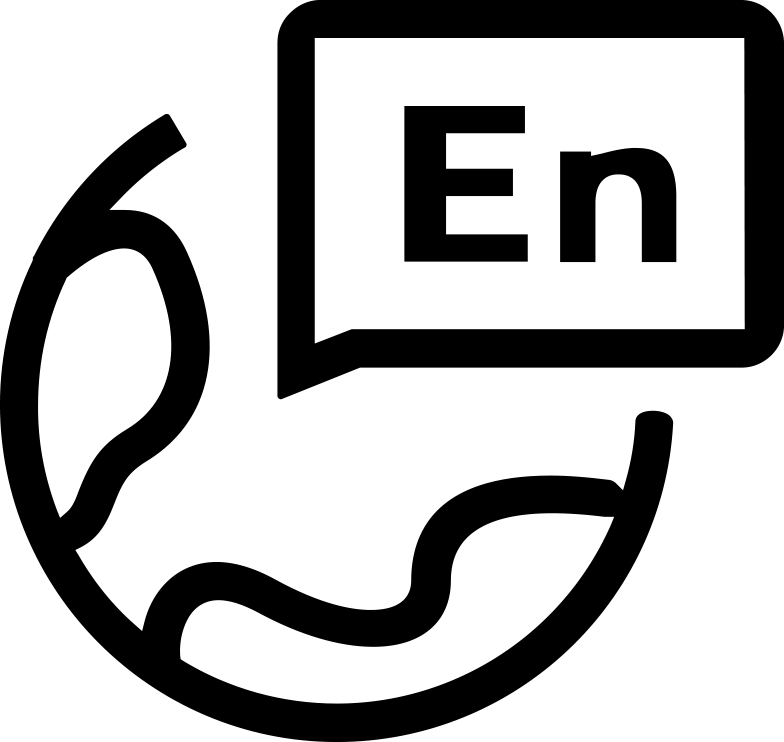.jpg)
作者简介:田文昌,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名誉主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与中国审判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国家检察官学院兼职教授,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名誉院长。
办好一个案件,可以防止一个错误,维护一次公正。而推动立法的改进,却可以防止一类错误,维护一片公正,帮助一批人免受不公正的追究。这正是“个案推动立法”的意义所在。因此,一个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律师,应将“以个案推动立法”视为自己的使命。
虽然这也是其他从事法律实务的群体即司法人员的使命,但是,由于中国的法治现状,在这方面,律师的作用更显重要,因为律师的感受更加直接、深切。
遗憾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尽管社会实践已经为立法部门的立法和修法提供了大量的案例和建议,但是,立法部门的工作却跟进不够,两者出现了较大的距离。加之基层司法机关常常“有法不依”,以至于律师界出现了一种普遍的悲情,所谓“死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尽管如此,我认为,既然“依法治国”已经是大势所趋,既然“个案推动立法”是律师的使命,我们还是要为完成这个使命作不懈的努力。
个案推动立法,这代人的使命
立法的发展离不开个案的推动。这种推动作用在法治化进程的初级阶段尤为重要。
我国法治建设三十多年来,立法的发展经历了几乎是从无到有的过程,其规模之大,速度之快,举世瞩目。然而,立法不仅要有成熟的技术,而且还要有丰富的经验,更重要的,还需要实践中千差万别的具体个案中反映出来的事实与规范之间的冲突作为参照。因为,有冲突,才有规范。冲突,既可以反映对规范的需求,也可以检验规范的合理性。对于立法,个案具有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
近年来,随着社会矛盾的不断加深和多样化,实际案例日益复杂,因个案引发的立法或修法的契机不断出现。关键是,立法机关能否抓住这种契机。
2003年3月,广州务工的湖北青年孙志刚被收容并被打死一案,引发《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是否应该废除的全民大讨论,我也在第一时间表态支持废除。由著名宪政学者、全国人大秘书局副局长蔡定剑主持的“公民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对《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的案例分析会”就是在我们京都律师事务所召开的。同年6月,该法被废除。遗憾的是,在这之前,收容遣送制度已经实施多年,近似的案例一再出现,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直到付出孙志刚被收容并被打死这样惨重的代价。
和孙志刚案稍有不同,吴英案以一审死刑的可怖代价只是换来了终审的免死,却没有导致法律的修改,也令我扼腕叹息。吴英案涉及的集资诈骗罪,来源于多年前的沈太福、邓斌非法集资案,针对的是非金融机构的个人或单位向社会上不特定多数人非法集资、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然而,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需求,以及国家金融体系的缺陷,催生了民间金融市场。在国有银行融资渠道不畅的情况下,民营企业只得向民间资本融资,以至于出现大量的民间借贷和相关冲突,冲突的根源还在于立法没有及时跟上,吴英案便是反映这种冲突的典型。
综上,大量的案例都显明,在新的问题刚刚暴露时,如何更积极、更主动、更及时地发挥“个案推动立法”的作用,是摆在立法者面前的重要问题。如何对典型个案的分析和总结,以此考察立法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及时提出修法建议,并大声呼吁,促使立法者及时解决这些问题,也是我们律师应尽的责任。而我们的立法机关应当多倾听律师的声音,做出积极的回应。
个案推动立法,现状不容乐观
诚如上述,近年来,实践中足以提醒法律修改的典型案例并不在少数,出自律师、法律研究者等群体的建议也不在少数,但引起重视的不多。下面,仅仅根据我个人的办案实例,站在一个律师的角度,为这样的法治现实做一个见证。
第一个例子。建议修法,以明确刑法第205条规定的“虚开增值税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的构成要件。
立法机关设立这个罪名的背景是,1994年实行税制改革后,出现了一些个人和单位利用开具虚假增值税专用发票骗取国家税款的行为。这种行为不同于原来意义上的逃税罪,而是在没有任何经营活动的情况下,凭借虚假的增值税发票骗取国家税款,其危害后果十分严重。因此,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以补充罪名的方式出台了专门规定,1997年的刑法则设立了这个罪名。
但是司法实践中的个案纷繁复杂,开具虚假增值税发票的情形千姿百态,其中包括只有虚开行为并无骗税目的和骗税结果的情况。这些情况的出现,致使在理论和实践中对该罪构成要件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分歧,以至于出现了“行为犯”、“目的犯”、“结果犯”之争。
事实上,这种行为侵犯的客体只是发票管理制度而并非税收管理制度,且客观上没有造成国家税款损失,其危害性远远小于作为结果犯的逃税犯罪。但一旦被定罪,其处罚却远远重于逃税罪。
出现这种量刑严重失衡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立法表述不明确。虽然立法的滞后性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当问题已经显现时,就应该尽快修法以使明确。否则,就会导致实践中出现大量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即对于同样性质的行为,在判决时出现罪与非罪,甚至死罪与非罪的天壤之别。
为此,我在2011年发表了题为《对虚开增值税发票罪构成要件的表述亟待修改》的专题论文,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呈交了修法建议,建议明确该刑法条文表述的含义,强调构成该罪必须具有骗税的目的和结果。
遗憾的是,这个建议至今未被采纳,司法实践中仍是乱象丛生。
第二个例子。建议设立行业舞弊罪。
多年前发生在江苏扬州的全国首例彩票诈骗案,其行为特征类似内幕交易,应属于一种行业舞弊行为。由于我国刑法没有舞弊罪,这种行为又确实具有较严重的危害后果,检察机关只好以诈骗罪提出指控。开庭审理中,我们律师提出了不构成诈骗罪的辩护意见,法院虽然重视律师的意见,但迫于立法方面的局限,也迫于社会的压力,只好折中一下,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其实,如果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这个案子是不应当定罪的。
这个案例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补充立法、明晰个罪界限的问题。同样遗憾的是,我们的立法建议没有得到立法机关的回应。立法的滞后迫使法官在无法可据的情况下,还是沿袭以前类推的做法,将刑法没有规制的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纳入犯罪圈,破坏了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也导致刑法中个别罪名成为典型的口袋罪。
第三个例子。建议废除新刑法第306条规定的律师妨碍作证罪。
早在1994年,即增设这个罪名之前,我就通过李强律师在代理案件中被非法拘禁一案,在《市场法制导刊》上提出了刑事辩护律师调查取证难的问题。
306条的立法依据是,1996年修改的刑诉法将律师介入刑事案件的时间提前到了侦查阶段,设立这个罪名主要是担心律师会妨碍侦查。然而,这只是一种理论的假设,并没有,也不可能有已经发生的案例为依据。因为在此之前,律师是不能在侦查阶段介入的。当时我就预感到,增设这个罪名更可能引发的后果是,司法机关借此对律师进行职业报复。
果不其然,设立这个罪名后,发生了一系列用这个罪名对律师进行职业报复的案例。因此,我加大了呼吁取消这个罪名的力度,如2004年,我在《西部法苑》上提出,刑法306条是悬在律师头上的一把利剑,随时可以被职业报复者用来斩断律师的职责和职业生涯。除了中国,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这样的立法,对律师单设这样的罪名具有明显的职业歧视性。
2009年11月,即李庄事件发生的前一个月,我还将“律师向被告人宣示案卷内容”列为全国律协刑委会2009年年会的一个议题,进行研讨,并发表题为《律师有责任向被告人告知案卷内容》的演讲。不仅如此,我还多次给立法机关写信,要求取消刑法306条。
遗憾的是,在当时,我的呼声没有引起立法者、甚至没有引起律师同行足够的重视。
近年来,尤其是李庄事件发生后,律师界和学术界关于废除刑法第306条的呼声日益强烈,我倍感欣慰,并继续推动。广西北海四律师被抓事件发生后,律师界和舆论界一片哗然,我旗帜鲜明地指出:“这是多年来利用刑法306条对律师进行职业报复的急剧升温,是对刑事辩护制度的严重冲击”,并再次呼吁废除刑法306条。
在强大的舆论冲击下,此次刑诉法再修改总算修改了与刑法第306条相对应的条款。这一修改表明,刑法306条的修改已成为必然。但是,在我看来,仅仅修改是不够的,彻底废除刑法306条才是正道。
我认为,在中国法治发展的初级阶段,出现立法跟不上实践的问题不足为怪。重要的是,不能对这些问题置若罔闻,更不能简单、盲目地去顺应和注释法条。应当发现和剖析这些问题背后的深层原因,干脆利落地立法和修法。
个案推动立法,同志仍须努力
“个案推动立法”,我们在忧虑之余还须看到立法机关并非毫无作为。近年来,律师界的努力,有些获得了成功,有的获得了部分成功,有的引起了立法者的重视,有的已经摆上了立法者的议事日程。
仅我个人参与的实践来说,也获得过多次成功。仅举两例。
第一个例子。对于1997年刑法增设第193条规定的贷款诈骗罪、第194条规定的票据诈骗罪和金融凭证诈骗罪、第195条规定的信用证诈骗罪的新罪名,我建议增设过渡罪名。
对于这类罪名,由于司法实践中难以准确认定行为人主观目的,导致出现大量同行为不同罪名的比较严重的司法不均衡现象。有些司法机关出于谨慎原则,在难以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情况下,作出不起诉或不定罪的判决;但也有些司法机关以后果推论目的,将那些因客观原因无法归还而造成危害后果的行为,视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而定罪,形成罪与非罪,甚至死罪与非罪的悬殊差异。这种差异不仅损害了被告人的权益,也影响了司法认定的统一性,使一些司法人员无所适从,造成很不好的社会影响。
针对这个问题,我曾结合一些具体案例发表了《金融诈骗罪的两个误区及立法构想》的专题论文,并向立法机关提出具体的修改建议--对以上几种犯罪增设相对应的过渡性罪名,即对于那些在取得金融机构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的过程中确有欺骗手段并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却难以认定其确有非法占有目的的行为,增设一种处罚较轻的罪名。我认为,这样既可以避免因实践中把握界限不清而形成的司法不均衡,也可以惩处和警示那些虽不具有诈骗动机却向金融机构转嫁风险的行为。
后来,立法机关在刑法修正案(六)中增设了“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的过渡罪名。这,虽然不能说是某些人以一人之力促成的,却鲜明地体现了“个案推动立法”的重要作用。而我个人的努力,至少构成了民意表达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二个例子。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争取对案卷内容的知情权。
关于律师会见时,能否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出示案卷,与之核实证据内容这件事,过去在立法上没有明确规定,并且在理论上颇有争议,以至于有律师因在会见时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证据而被追究刑事责任。由于律师不能行使该项权利,严重限制了被告人的质证权。这一问题的实质,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否享有对案卷内容的知情权。
为此,我在反复研究和考察之后,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上多次发表意见,并在《民主与法制时报》上发表论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证据享有知情权》。在刑诉法再修改过程中,我与其他有关方面的人士还据理力争。
最后,立法机关在新刑诉法第37条明确规定了律师会见时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这一规定对于保障被告人充分行使质证权具有重大意义。
正因为“个案推动立法”还是有不少成功的案例,我们信心不灭。尤其是,我们认识到“个案推动立法”是我们这代人的历史使命,再难也会坚持下去。这样,当我们回顾人生的时候,至少可以说,我们努力过了!
有鉴于此,与同行或媒体人士谈起这方面的工作,我总喜欢说:“没有别的办法,我就只有喊。不喊白不喊,喊了也白喊,白喊也得喊,喊多了就不白喊。”
正是本着这种精神,今年5月,知名演员黄海波嫖娼被收容教育一案发生,我们律师所立即采取行动,仅仅过了一个月,就做出一个重大举动,即媒体所言:“6月18日,京都律师事务所联合江平、陈光中等133位知名专家、律师,向全国人大法工委递交建议书,呼吁废除收容教育制度。”
针对此事,我们所的发言人杨大民还对媒体表示:“希望此举能够引起立法机关的重视,引起人们对限制人身自由行为的思考。律师不能像其它职业那样仅仅是‘老老实实演戏,本本分分做人’。通过典型的个案推动国家的法治建设,乃是我们律师应尽的社会责任。”这,也应当是我们每一个律师的追求和使命。
分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