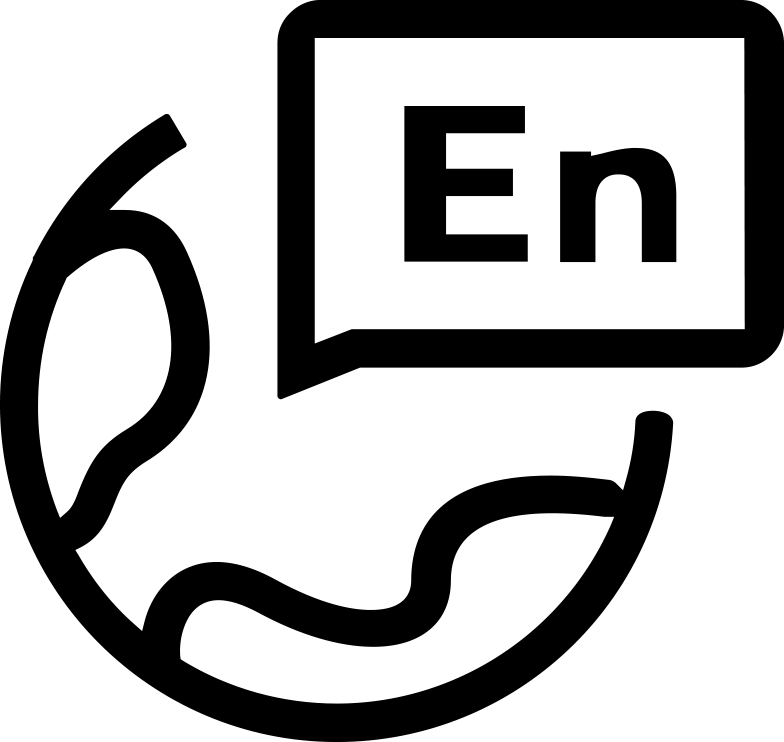在深圳打工的80后男子王鹏,出售2只和“待售”45只自己繁殖的、被一审判决认定为“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鹦鹉被判刑五年,近日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热点。众多媒体纷纷予以报道,对此判决的评论褒贬不一,有的人从保护野生动物的角度,在评论中提出鹦鹉可怜孩子可怜,但直指被告人本人是罪魁祸首,还有的法律人士评论称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是违反常识的荒唐判决,凡此种种……
那么此案的被告人王鹏到底是否有罪?该判决到底荒唐不荒唐?笔者仅结合本案一审判决书,认为从判决书中体现的现有证据情况来看,并不能认定王鹏构成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且量刑畸重。同时认为该判决书不管是从证据的审查判断、裁判的说理性等方面相较目前很多判决书来说还是有值得肯定之处的,显然单纯的用荒唐来形容此案也略显不妥,但总体来说该判决确实存在诸多重大的认定错误问题。
笔者现根据本案判决书中罗列的证据、裁判说理的内容,结合野生动物保护的相关法律规定以及有关野生动物的专业知识,从以下五个方面对该案进行探讨:
一、判决认定45只鹦鹉“待售”是犯罪未遂,属于事实认定错误,导致法律适用错误
判决书第11页:“另还查获45只列入《公约》附录二的被保护鹦鹉待售,属犯罪未遂,依法可以比照既遂犯减轻处罚。辩护人认为该45只鹦鹉不是用于出售的意见与查明的事实不符,不予采纳。”
首先,在此需说明下,该事件新闻媒体上多以“因售卖两只自养鹦鹉被判5年”为标题,于此没必要深究发文者的目的。可笔者还是觉得这样的标题容易引人误解,根据《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及《解释》第十条,两只绿颊锥尾鹦鹉的量刑标准在五年以下,又根据《刑法》第九十九条以下包含本数,即出售两只涉案鹦鹉法院可以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但并不是说只是因为出售这两只鹦鹉就判了被告人王鹏五年,判决书说得很清楚,法院在认定王鹏出售2只鹦鹉的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情况下,对其家里驯养繁殖的另外45只鹦鹉认定为了犯罪未遂,是综合判处了王鹏五年有期徒刑。
其次,判决指出王鹏家里的45只鹦鹉属于待售,认定为犯罪未遂显然是错误的。本案根据同案被告人谢田福的供述,在王鹏家里查获了45只鹦鹉,也就是说45只鹦鹉被查获,是因为同案被告人供述后,侦查机关去王鹏住处查获的,而不是比如王鹏正在在市场上售卖时等情况下查获的,而王鹏本人又有自己稳定的工作,并不是倒卖鹦鹉的商贩。根据刑法的规定,犯罪未遂是指已经着手实行犯罪,但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而构成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未遂,必须是已经着手实施出售的行为,比如正在拉着鹦鹉赶往市场的路上、正在实施摆摊、吆喝、讨价还价行为等等,此时如因被抓获归案等原因未能售出涉案物品,从而被认定为未遂是正当的。而本案中是在家中查获涉案鹦鹉,该鹦鹉出于饲养状态当中,此时的行为是饲养行为,至于将来这些鹦鹉是出卖还是一直自养,通过该饲养行为本身无法确认。未遂犯处罚的根据是行为所造成的侵害法益的紧迫危险状态,饲养行为本身并不会造成对野生动物资源的侵害,更不会使野生动物资源处于紧迫危险的状况。根据《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针对破坏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资源活动的处罚,仅针对收购、运输、出售的行为,自有状况下的饲养行为并不包括在内,所以认定被驯养的45只鹦鹉是待售、构成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未遂显然于法无据,是错误的。
再次,假定王鹏本人在供述中称饲养的余下45只鹦鹉也是为了出售,那么饲养行为是否就可以被认定为出售行为的犯罪预备了呢?根据刑法,犯罪预备是指为了实行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但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着手实行犯罪的特殊形态,犯罪预备处罚的依据是行为对法益具有一定的抽象危险。举个简单例子,准备杀人而去商店买了一把刀,而买刀的行为对人身具有一定的抽象危险,自然去商店买刀的行为就是故意杀人罪的犯罪预备行为。而本案准备出售而饲养的行为,饲养行为本身对野生动物保护并不会产生任何抽象危险,自然以出售为目的而饲养的行为不是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犯罪预备行为。如果王鹏为了出售余下45只鹦鹉,而事先去调查市场位置、询问市场销售价格、寻找购买人等,这些调查、询问、寻找购买人等的行为笔者倒是觉得可以认定为出售行为的犯罪预备行为。由此可知,王鹏的行为也不能构成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的犯罪预备。另,前文假设的王鹏供述称饲养的45只鹦鹉是为了出售,笔者认为王鹏的该供述属于刑法理论上的犯意表示行为,只能表明王鹏具有真实的出售涉案45鹦鹉的犯罪意图,但因饲养行为本身不能为出售行为制造任何条件,更没有从事任何与出售相关的犯罪行为,所以在案的45只鹦鹉根本不能成立犯罪(含预备犯、未遂犯,当然犯意表示本身就不成立犯罪)。
二、认定涉案鹦鹉属于《刑法》保护对象的裁判依据不足
(一)《野生动物保护法》没有对“野生动物”赋予明确的法律概念,认定涉案鹦鹉属“野生动物”存在法律认定上的障碍
新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已于2017年01月01日开始实施,但遗憾的是因学理上“野生动物”的定义并没有达成共识,新法仍没有赋予“野生动物”明确的法定概念,仅是规定本法所保护的野生动物,是指珍贵、濒危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和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很明显,这里的“野生动物”并不包括所有的野生动物,也就是说目前我国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实行等级保护制,而绝大多数野生动物是被排除在法律保护范围之外的,法律的名称与其内容本身就不一致。当然关于本案,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新法仍采用了旧法中仅规定该法所保护的“野生动物”范围的做法,对理论和司法实践中长久存在争议的“野生动物”认定的问题,立法上没有任何进步,实属令人遗憾。
实践中,有一种广泛被接受的“野生动物”的定义是“生存于野外的非家养动物”,野生动物的定义应定位在一个与家养动物相对的角度上。而本案王鹏所出售的两只鹦鹉是其驯养繁殖的、判决书亦认可涉案鹦鹉系“人工变异种”,毋庸置疑这种“人工变异种”是有别于一般概念上的野生动物的。由此,可以说本案是一起因立法对“野生动物”的法定概念不明,导致立法功能消减、司法脱离实际的又一个典型案例。
(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对“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内涵的表述严重滞后,导致涉案鹦鹉被错误地直接归类为《刑法》所保护的“野生动物”
本案判决书载明:“本案所涉的鹦鹉虽为人工驯养,亦属于法律规定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法院作出这样的认定并不是没有道理,其根据就是《解释》第一条:“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包括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国家一、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列入《公约》附录一、附录二的野生动物以及驯养繁殖的上述物种。”
笔者同样认为,身为执法者,依法办案毋庸置疑,但在法律适用的过程中,不能仅根据法律的字面含义对案件事实进行简单认定,特别是时过境迁,立法环境和社会、自然环境均发生重大改变的情况下,应综合立法目的、立法背景等因素进行综合评判,以期能够正确适用法律。《解释》的立法目的在解释中规定的很明确,就是依法惩处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犯罪行为,鉴于类似案件屡次发生,而新的司法解释尚未伴随新的《野生动物保护法》更新的情况下,现就《解释》出台的背景进行阐释,以期还原《解释》中提到的“驯养繁殖的上述物种”内涵的真相,以达到正确司法的目的。
首先,《解释》制定于2000年,上个世纪,在我国除极少数几种野生动物的驯养繁殖技术达到了子二代水平(即野生来源的野生动物亲本,经人工驯养繁殖,能繁殖到两代以上),大部分野生动物的人工驯养繁殖活动,只存在于动物园和一些野生动物救护驯养繁殖基地,并且没有达到繁育子二代的水平,有些甚至是直接野外捕获再圈养起来的野生个体;或者达到了繁育子二代的水平,但这种驯养繁殖包含了以未来放归野外为目的的野化过程,这些人工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不是以商业利用为目的,而是以增加种群数量达到珍贵、濒危物种的种群扩增,具有野生动物异地保护的意义。因此,这类人工驯养的野生动物,的确属于野生动物的范畴。
那一时期,我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国家一、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列入《公约》附录一、附录二的野生动物中,几乎没有任何一种动物,在当时经过人工驯养繁殖,成为家庭饲养的家养动物。除了人类历史早期被驯化的动物,如家犬,尽管是人工驯养繁殖的狼,但人们普遍把犬作为家养动物,而不会作为人工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因此在《解释》颁布的时期,把人工驯养的野生动物或野生动物驯养繁殖的后代都看作是野生动物的范畴,是没有多大争议的,符合当时的立法条件。
其次,近些年,随着人工驯养繁殖技术的不断提高、国内外养殖技术交流活动更加频繁、便捷,养殖设备、环境的不断改进等等因素,使得人工驯养繁殖活动中人为干预下动物的基因变异、形态等变化的速度极大的提升。以前需要千百年驯化时间才能最终作为家养动物饲养的状况,在当下可能仅需要几年甚至更短时间即可以做到。
再次,这种利用野生动物种源,人工驯养繁殖而出生的动物,由于是在家养状态下出生的,经过人工圈养以后,这些野生动物的行为乃至遗传构成都发生了变化,如果将这些人工繁殖的野生动物放归其自然生境,这些野生动物将很难存活和繁殖,因为他们已经丧失了在自然环境中觅食、躲避天敌、寻找配偶的能力。这种情况下,应该将其归属为家养的观赏用宠物而不是野生动物。而本案中,根据新闻媒体报道,王鹏的爱人任女士说:“应该是别人家养的宠物鹦鹉飞出来的吧,当时它落在工厂干活的地方。不会飞,不知道是饿了还是生病了,他们在那干活,看到了就把它捡回来了。而且他们说很亲人,过去逗它它就过来了。野生的话它肯定会飞走,肯定会怕人的。”当然任女士的说法并不能直接证实涉案绿颊锥尾鹦鹉不是野生的,但根据其描述以及常识,至少可以得知该鹦鹉对人并不陌生,不怕人。所以不能排除王鹏所拥有的第一只绿颊锥尾鹦鹉就是人工圈养繁殖而来的可能性。那么该鹦鹉再次繁殖产生的后代更进一步减弱了野外生存能力和繁殖能力,不管是从野生动物资源角度还是从社会效益角度,如果再将其认定为野生动物显然缺乏科学性和合理性。因此,在当下把人工驯养的野生动物或野生动物驯养繁殖的后代还看作是野生动物,是与社会实践脱节的,自然也不符合《解释》出台的目的。
所以,《解释》中的“驯养繁殖的上述物种”,结合当时的立法目的和立法背景应该理解为上述物种野生型的人工驯养繁殖个体或种群,并且没有发生显著的遗传变异,没有产生明显的形态和基因变化的物种,这样的动物才属于受《刑法》保护的野生动物。至于名录和附录中相同物种名的非野生动物,也就是说如果上述物种存在家养型,即商业训化、家庭宠物化、实验动物化的动物,则不应属于野生动物的范畴,也就不在《野生动物保护法》保护范围之内,不能再适用于《野生动物保护法》和《解释》。
综上,仅根据《解释》的字面含义,将涉案人工变异种的绿颊锥尾鹦鹉直接认定为属于《刑法》所保护的“野生动物”,缺乏客观性,更不符合立法目的,亦是在没有分析现有《解释》出台背景的情况下,作出的不负责任的裁判。
三、涉案的4只玄凤鹦鹉是否为珍贵、濒危野生动物问题,判决书存在事实认定错误的问题
判决书表明:“无证据证明玄凤鹦鹉是珍贵、濒危鹦鹉。”此说理的部分存在因专业知识缺乏的问题导致的事实认定错误。
2003年,国度林业局《关于发布商业性经营利用驯养繁殖技术成熟的梅花鹿等54种陆生野生动物名单的通知》,名单中载明,鹦形目中含分凤头鹦鹉科和鹦鹉科,两个科中合计包含五个属种,分别是凤头鹦鹉科含鸡尾鹦鹉(别名玄凤、红耳鹦鹉)。鹦鹉科含虎皮鹦鹉(别名娇凤、彩凤、阿苏儿)、费氏牡丹鹦鹉(别名棕头牡丹鹦鹉、红牡丹鹦鹉、费希氏情侣鹦鹉)、桃脸牡丹鹦鹉(别名小鹦哥、桃脸、蔷薇鹦哥、桃脸情侣鹦鹉)、黄领牡丹鹦鹉(别名黑头牡丹鹦鹉、黄领黑牡丹、黄襟黑牡丹鹦鹉、伪装情侣鹦鹉)四个属种。
而《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以下简称“《公约》”)(CITES)附录二载明,受保护的鹦鹉类别系鹦形目所有种(除被列入附录一的物种,且不包括未列入附录的桃脸牡丹鹦鹉、虎皮鹦鹉、鸡尾鹦鹉和红领绿鹦鹉)。《公约》附录二明确将鸡尾鹦鹉即本案中的玄凤鹦鹉排除在《公约》的附录之中。
另,鸡尾鹦鹉即玄凤鹦鹉系非原产于我国的野生动物,其分布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塔斯马尼亚及其附近的岛屿。既然玄凤鹦鹉非原产于我国,在国内又属于驯养繁殖技术成熟且可以商业经营利用的物种,自然不会包含在我国野生动物保护名录中,其又被《公约》排除在保护范围之外,同样不是《公约》所保护的野生动物,那么玄凤鹦鹉在时下当然就不是珍贵、濒危的野生动物,对其进行出售等经营行为自然不被法律所禁止,所以判决书对此问题的表述缺乏客观真实性,不能实现司法的教育、普法功能。
四、本案中的鉴定问题可能存在严重缺陷
从本案判决书对鉴定问题的描述上看,涉案鹦鹉应该是都进行了司法鉴定。但王鹏一审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中称,现有证据仅能认定王鹏出售给谢田福2只受保护的动物,其理由是因为谢田福和王鹏均说6只鹦鹉中2只是小金太阳鹦鹉(绿颊锥尾鹦鹉),另外4只是玄凤鹦鹉,两者供述能够一一对应,所以犯罪数额应认定为2只鹦鹉。而法院最终认定涉案数量时却没有根据鉴定意见,而是采信了两被告人的相一致供述。问题就出来了,既然都进行了鉴定,为何最终却采信两被告人供述,仅认定为两只?
笔者认为本案判决出现上述情况并不稀奇,目前野生动物保护的案件,之所以出现重大争议,引起舆论的关注,很多是因为司法鉴定意见对物种的鉴定缺乏科学、谨慎的态度,笔者目前正在承办的另一起野生动物保护的案件中,其鉴定过程,仅是鉴定人凭眼睛观察,之后查阅文献资料,就因为物种名与《公约》规定的一致就得出涉案动物系“野生动物”的鉴定意见。
殊不知,在野生动物驯化为家养动物过程中,尚存在野生与家养之间的各种过渡类型,定义一个物种是野生还是家养往往需要综合考虑该物种的生物学、遗传学、驯化历史和社会、经济等等因素才能作出科学、合理的判断。类似仅凭眼睛观察的方式进行的鉴定,明显缺乏鉴定应有的科学态度和精神,是极端不负责任的,当然这也与目前国内野生动物保护领域缺乏统一、规范的鉴定细则有关。总之,当下对野生动物的鉴定尚存在重大问题亟待解决,只有明晰鉴定标准和方法等,对待鉴对象进行科学鉴定,这样的鉴定意见才能够在刑事诉讼中作为定案的证据使用,否则根据粗略的方法得出的裁判结果根本不能服众。
五、假使本案构成犯罪,对量刑问题的探讨
根据《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及《解释》第三条,涉案数量达到6只以上的属于情节严重,应在五年以上量刑,涉案数量达到10只以上的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应在十年以上量刑。而本案认定的数额是2只,如果单纯认定数量为2只的犯罪既遂,法定刑固然应在五年以下。前文讲到,之所以判了被告人王鹏五年,是法院在认定王鹏2只既遂和45只未遂的情况下,综合判处的刑期。以下笔者从45只鹦鹉未遂成立与不成立两个角度分析法院的量刑是否正确的问题。
首先,假定出售45只鹦鹉能够成立犯罪未遂的情况下,判处王鹏五年有期徒刑已经是最轻的刑期了,判决并无错误。
根据“两高”《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诈骗既有既遂,又有未遂,分别达到不同量刑幅度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处罚;达到同一量刑幅度的,以诈骗罪既遂处罚。据此,对单纯以犯罪数额作为升格法定刑适用条件的犯罪类型,首先要分别根据行为人的既遂数额和未遂数额判定其各自所对应的法定刑幅度,未遂部分还需同时考虑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之后根据比较结果,如果既遂部分所对应的量刑幅度较重,或者既、未遂所对应的量刑幅度相同的,以既遂部分所对应的量刑幅度为基础酌情从重处罚,反之,如未遂部分对应的量刑幅度较重的,则以该量刑幅度为基础,酌情从重处罚。
而本案中,既遂的数量是2只,法定刑幅度在五年以下,未遂的数量是45只,法定刑幅度在十年以上,显然未遂部分对应的法定刑幅度较重,但根据《刑法》第二十三条,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之规定,本案应属可以减轻处罚的情况,又根据《刑法修正案(八)》第五条:“将刑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修改为:“犯罪分子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的,应当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本法规定有数个量刑幅度的,应当在法定量刑幅度的下一个量刑幅度内判处刑罚。”可知,减轻处罚后,45只未遂数量对应的法定刑也只能确定在十年以上的下一个量刑幅度即五年到十年之间。
综上,判决在认定饲养的45只成立犯罪未遂的情况下,选择五年有期徒刑已实属最轻。法院在刑期的选择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如此裁判也并不荒唐。
其次,正如前文所述,判决认定饲养的45只鹦鹉属“待售”是犯罪未遂是错误的,在不成立犯罪未遂的情况下,判处王鹏五年有期徒刑就属于量刑畸重。
由此,因为犯罪未遂不能成立,甚至饲养的行为连犯罪预备都不能构成的情况下,单纯的出售2只鹦鹉的行为,结合所售2只鹦鹉系王鹏自行繁育而来的人工变异种,并不会加剧绿颊锥尾鹦鹉种群濒危程度的情况下,判处王鹏缓刑甚至免于刑事处罚都是完全合情、合理和合法的。
综上,法治的发展,离不开个案的推动,通过对个案的学习、研究、褒扬、批评和建议,能够有针对性的总结法治建设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近日媒体关注的该深圳鹦鹉案,不管是立法者、司法者,还是像笔者这样的法律从业人员,通过本案大家都在总结、纠正和提高,只是希望在个案推动法治的过程当中,代价不要太大,更不能使不该受到刑事追究的人遭到刑事处罚,造成冤假错案,诚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