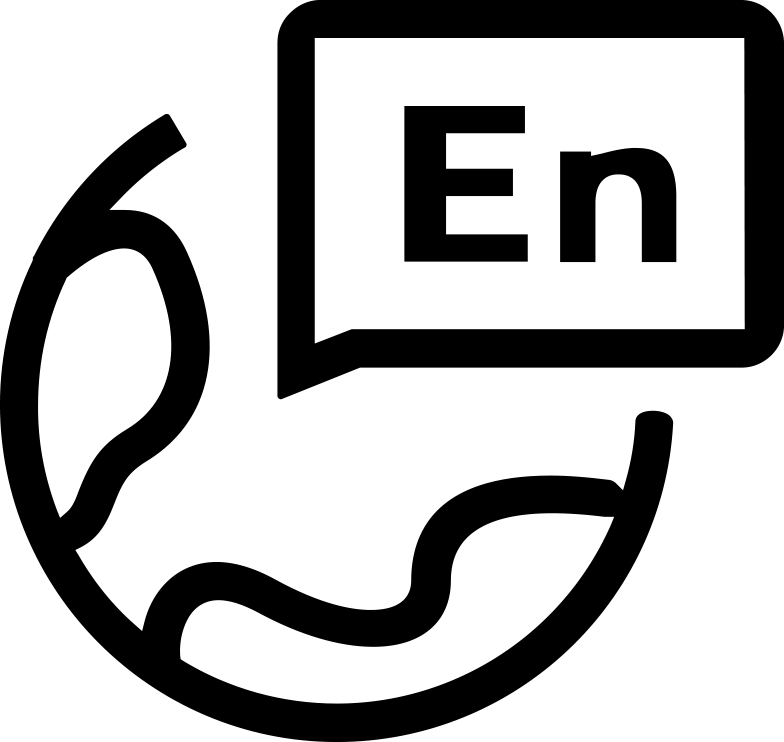民事公益诉讼作为一项新的诉讼制度于2012年随着新的《民事诉讼法》的实行得到了确认,但是短短一个条文,寥寥数字是无法涵盖一个新制度的完全内涵的。如何确认民事公益诉讼的客观范围,划清受案范围的标准是摆在我们面前不得不解决的问题,本文从公共利益的解释出发,结合案例试图厘清民事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为民事公益诉讼的社会公共利益划定标准。
关键词:民事公益诉讼客观范围公共利益不特定多数人利益
引言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令世人瞩目。然而快速的发展往往伴随着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伴随着对社会公共资源的恣意攫取与破坏,正如“公地悲剧”[1]所描述的一般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追逐市场利益的人们对环境的破坏,不仅侵害了社会的环境利益而且侵害了他人的财产利益。同时政府对市场经济行为的规范不力,商人对市场利润的不当追求也造成了消费领域中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环境污染和消费者权益损害无疑是当今中国最具社会影响性的不法行为。为了从法律层面规制这些行为,我国2012年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了“公益诉讼”,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然而,关于公益诉讼的具体客观范围,具体实施程序,与普通诉讼程序的区别等问题正如张卫平教授所说的该条文的规定只是从原则层面解决了“公益诉讼”有无的问题,关于“公益诉讼”的具体客观范围以及制度性规定并没有得到立法层面的明确[2]。本文在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之上试图对民事公益诉讼的客观范围即民事诉讼法公益诉讼中规定的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具体案件类型的指向范围作一番界定。
公益诉讼的客观范围,简单表述下来也就是公益诉讼可以在那些类型的案件中得到适用的问题。目前我国的立法采用列举的方式明确了污染环境和消费者权益损害者两类诉讼类型可以适用公益诉讼,另外用“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对公益诉讼的适用范围作了一个兜底性的概括表述。然而,何谓“社会公共利益”这个历久弥新的课题在国内外众多政治学、法理学和法哲学专家的研究中都未能得出一个被普遍认同的结论甚至方向[3]。学者哈耶克甚至认为:“社会公共利益”只是一种学科意义上的抽象,不是实在的政治和法律概念[4]。但是,既然我国立法中规定了“公共利益”,在无法变更现有立法,又难以找到更确切的能表达立法者原意的概念时,我们只能利用法律解释的方法对“公共利益”作一番界定,并且只有在明确“公共利益”的基础之上,方能对民事公益诉讼的客观范围作一个明确的表述。
公共利益的历史解释
公共利益从字面上来看就是公众的利益、大家的利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对这一概念也有不同的解释。公元前5-6世纪的古希腊城邦国家制度造就了一种“整体国家观”。与“整体国家观”相联系的是具有整体性和一致性的公共利益。公共利益被视为一个社会存在所必需的一元的、抽象的价值,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目标[5],即此时的公共利益主要表现在国家利益,国家公共意志上。比如:亚里士多德把国家看作是最高的社团,其目的是实现“最高的善”,这种最高的善在现实社会中的物化形式就是公共利益[6],这是典型的以国家利益的概念来代替公共利益的想法;法学家乌尔比安以“公共利益”作为基础提出公法的理论也正是将公共利益限定在了国家利益的层面。到了18世纪,唯物学者爱尔维修则将公共利益定义为“大多数人的幸福”[7],试图从受益者的多寡来区分公共利益和私益,无独有偶,英国学者边沁也提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概念,“大多数人获得的利益”其实仅仅从公共利益的表面特征对其进行了表述,并没有对其实质含义进行界定。20世纪社会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庞德将利益分成了三层,试图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一是个人利益,即“直接涉及到个人生活,并以个人生活名义所提出来的主张、要求和愿望”。二是公共利益,即“涉及政治组织社会的生活,并以政治组织社会名义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8]。三是社会利益,即“涉及文明社会的社会生活,并以社会生活的名义提出的主张、要求和愿望”,庞德表述中的“公共利益”依然局限在国家利益的层面,然而笔者认为他所表述的“社会利益”的概念恰恰与我们民事公益诉讼中的“社会公共利益”的概念相近。即我们认为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公共利益”应当区别于一般的“国家利益”,而更关注与社会不特定人利益相关的社会福利,包括社会自然资源,消费者权益,平等就业权益等等。
民事公益诉讼中对“社会公共利益”的限定
关于“社会公共利益”的表述,我国学者中亦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社会公共利益应该有两层次含义:第一层为社会公共利益,即为社会全部或部分成员所享有的利益;第二层含义是指国家利益[9]。另外有学者认为应该分为三个层次即:“一为国家利益,此乃公共利益的核心,如国有资产;二为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此乃公共利益常态化的存在形式,如不特定多数消费者、环境污染受害人的利益、因垄断经营受损者的利益;三为需特殊保护的利益,此乃公共利益的特殊存在形式,是社会均衡、可持续发展必须加以特殊保护的利益,如老年人、儿童、妇女、残疾人的利益[10]。”
我们认为当语境为民事公益诉讼时,首先应当将直接受侵害的利益排除在外,梁慧星教授就认为:“何为公益诉讼,按照我的理解,它是指与自己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就是诉讼针对的行为损害的是社会公共利益,而没有直接损害原告的利益。我们这里用了‘没有直接损害’一语,当然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最终要损害个人的利益,但这里要作狭义的理解,只是指没有‘直接损害’。”也就是说公益诉讼必须要强调损害的发生与实际受损害的个体之间具有间接性和潜在性,而倘若表现为直接损害的话,即使损害的利益涉及到社会公益的范畴也应当排除在外而适用私益诉讼。具体来说,比如一条河流受到了污染,使得人们不得不放弃该处水资源而使得总的水资源更为紧张,间接减损了人们饮水的权利,这就是说该损害具有间接性,并没有直接损害某个人的利益,相反若是饮用了该河流的水而中毒,那么就成为直接的受损害人,而可以直接提起普通的侵权之诉;比如某大型企业规定只招收女性而不招收男性,这样的规定就是对所有想要应聘,求职的男性的潜在侵害,属于公益诉讼的范畴,若某位男性实际去求职而被告知该歧视行为,则是实际受到损害,可以以此提起侵权之诉。
以前文所述为依据,那么“国家利益”以及“特殊人群的利益”则应该与民事公益诉讼中的“社会公共利益”相区别。因为,国家利益和特殊人群的利益,他们的主体表现为独立的民事权利主体,对该利益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如国家利益归于国家、特殊人群(某一团体)的利益实际上归于该群体的个人,当这些个体利益受到侵害时,各个主体均有权寻求法律救济,进行诉讼时,各自的身份均自然地从民事权利主体转化为诉讼当事人,通过私益诉讼的方式去解决民事争议问题,而不必利用“公益诉讼”这一特殊的民事司法程序来进行。虽然国家利益通常表现为全民所有的利益受到侵害,如国有资产流失会间接地侵害普通人的利益,但是我们国家本身可以通过检察院行使公诉权,以及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而对这些受侵害的行为进行规制,同时国家的相关机构亦可以作为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民事诉讼主体而直接参与诉讼,因此不必将其归为公益诉讼的范畴。而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受损后,因为该主体的不确定性,使得无法找到直接法律关系主体而启动诉讼程序,因此,有必要超越普通私益诉讼的规定,赋予基于超越直接利害关系的机关、团体、组织甚至个人以诉权,使其能够根据其法定职能、价值追求、自我设定的相关社会职能来实现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11]。此外,许尚豪博士的《无主公益的特殊诉讼——我国民事公益诉讼的本质探析及规则建构》一文中以民事诉讼当事人正当性的角度出发,也正是论证了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作为公益诉讼中的社会公益范围的正当性,并巧妙论证了国家利益以及特殊群体利益的当事人应当作为私益诉讼的当事人进行起诉[12]。
“不特定多数人利益”在公益诉讼语境下的理解
因此,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公益诉讼案件类型,应当理解为涉及不特定多数人的社会共同利益的案件,也就是应当区别存在直接关系的私益诉讼(国家利益、特殊群体的诉讼亦可归类到私益诉讼之中),比如其中列举的污染环境案件,既有可能侵害特定人的财产或其他利益,也可能侵害了不特定人的财产或其他利益,而前者可以由直接受害人提起环境污染侵害之诉,而后者则是民事公益诉讼所适用的案件类型。而关于“不特定多数人利益”的理解,笔者认为应当满足以下几个条件:
首先,“不特定多数人利益”应当表现为利益的不确定性,此处的不确定性是指,在不同的语境下,不同的社会客观环境下,利益的具体所指有所不同,因为公共利益内容的保障或形成,必然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及国家社会情形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并且价值与利益的评判标准是不确定的,无法用一个以一贯之的标准来测定,是弹性的,浮动的。因此,此处的不特定多数人利益,决然不是某一恒定的利益,就如我国民事诉讼法在列举污染环境和消费者权益受损的案件类型以外,规定了“其他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并没有将公益诉讼限定在环境污染和消费者权益这两个标准之下,本身也就说明了该利益的不确定性。
其次,“不特定多数人利益”要求利益受体是不确定的多数人。这里应当对概念进行拆分,即首先是多数人的利益。多数人的利益并不必然指全体民众的利益,我国的立法也从来没有将全国人民作为“公共”的代称。当然仅仅用个人或者说特定的人来作为多数人的相反概念也不够明确,因为多少人才能称作多数人也无法律上的标准。德国1974年《税捐调整法》中将“公共”明确为非全体国民,同时至少亦非“某个圈子”的人[13],故圈子外的人可以算作是多数人,从某种意义上讲“圈子里的人”其实就是某些特定的人(因为有某种特征,因而会被视作是圈子里的人),因此“圈子外的人”本身也是不特定的人的表述;从另一个方面讲,多数人的利益并不必然是社会公共利益,群体性的利益也未必等同于公共利益,因为若是特定的某个群体,或可以确定的多数人的利益,利益直接归属于该特定的群体,我们依然可以利用私益诉讼来进行解决(可以找到直接利害关系人),比如三鹿奶粉一案中,虽然有众多消费者受到了有害奶粉的侵害,符合多数人的要求,但其受害主体是特定的,其基于直接受损害侵权的事实可以直接提起普通的民事诉讼解决。并且对于该人数众多的特殊情形,我国《民事诉讼法》专门规定了“代表人诉讼制度”,即通过诉讼代表人可以使得众多利害关系通过这一机制实现自己的诉讼请求。又比如该案中,三鹿奶粉的大量生产销售,其实也使得不确定的人群有可能食用该奶粉而发生损害,针对于这种潜在危害不特定人的行为,通过诉讼禁止该行为(而使不特定的人因此而受益)基于的就是保护公共利益,因此“受益人是不确定的多数人”是公益诉讼的必然要求。
最后,“不特定多数人利益”,必须要求该利益具有不可分性,具有整体性。这是公共利益的应有之义,公共利益是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但绝不是多数人利益的简单相加,因为,公共利益并不是私人利益的简单之和,并不是与私人利益相互对立,同一位阶的概念,而是凌驾于与个人利益之上的概念,是个人利益的抽象集合,公共利益既包含着每一个人的个人利益,同时又不可为个人所分割,正如美国约翰·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所说的:“亦即,有许多个人(可以说他们构成了一个共同体)要求或多或少的公共利益,但是如果他们都想享有它,那么每个人就必须享有同样的一份。公共利益所具有的数量不能像私人利益那样被划分,不能由个人按照他们的偏爱多要一点或少要一点。[14]”
关于民事公益诉讼客观范围的总结
首先,民事公益诉讼必须排除可直接适用私益诉讼的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案件,即民事公益诉讼必须适用于“间接损害”的案件,而不得是“直接损害”的案件,这是适用民事公益诉讼的必要前提。同时,该前提条件也要求,民事公益诉讼的诉讼目的只能归结于社会公共利益,凡是有个人利益或其他特定利益的目的的均不得适用民事公益诉讼。
其次,民事公益诉讼中的其他社会公共利益可以界定为“不特定多数人利益”,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应当理解为在不同的语境条件下存在于不确定的多数人的整体,不可分的公共利益。比如健康的生态环境、平等就业的权益、公平消费的权利等等。该利益并不为某个人或某特定群体的人独自享有,而是表现为不特定的人均有享有的可能性。
最后,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基础上,可以明确污染环境、损害消费者权益的并且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应当作为民事公益诉讼适用的案件,并且其他的法律规定不得于此相冲突,排除这两类案件的适用。相反,其他法律法规应当对这两类重点注明的民事公益诉讼类型进行相关制度的深化构建。
结语
明确民事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仅仅是完善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一小步,如何规范民事诉讼主体,如何与普通诉讼程序进行衔接,乃至如何执行等问题依然摆在我们面前,作为一种新的特殊诉讼制度,未来的路任重而道远,未来的民事公益诉讼还亟待更多的法律人去实践去完善。
注释及引用:
[1]参见哈丁:《公地的悲剧》,载于《科学》,1968年。
[2]参见张卫平:《民事公益诉讼原则的制度化及实施研究》,“实际上,该条规定并不是关于民事公益诉讼的制度性规定,而仅仅是一个关于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则性规定。也就是说,只是原则上确认对某些领域中侵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可以由非直接关系的主体提起诉讼,通过诉讼维护公共利益。”载于《清华法学》,2013年第4期,第7页。
[3]李凌碧著:《冲突与选择:民事公益诉讼与普通民事诉讼的衔接问题研究》,华东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10页。
[4]参见[英]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著,冯克利译:《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思想精粹》,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93页。
[5]参见胡鸿高著:《论公共利益的法律界定——从要素解释的路径》,载于《中国法学》,2008年第4期,第56页。
[6]参见胡建淼、邢益精著:《公共利益概念透析》,载于《法学》2004年,第10期。
[7]参见赵震江著:《法律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4-245页。
[8]转引自胡鸿高著:《论公共利益的法律界定——从要素解释的路径》,载于《中国法学》,2008年第4期,第57页。
[9]参见颜运秋著:《公益诉讼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6-27页。
[10]韩波著:《公益诉讼制度的力量组合》,载于《当代法学》2013年,第1期。
[11]张卫平著:《民事公益诉讼原则的制度化及实施研究》,载于《清华法学》,2013年第4期,第8页。
[12]参见许尚豪著:《无主公益的特殊诉讼——我国民事公益诉讼的本质探析及规则建构》,载于《政治与法律》,2014年,第12期。
[13]转引自潘申明著:《比较法视野下的民事公益诉讼——兼论我国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建构》,华东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4]转引自李凌碧著:《冲突与选择:民事公益诉讼与普通民事诉讼的衔接问题研究》,华东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