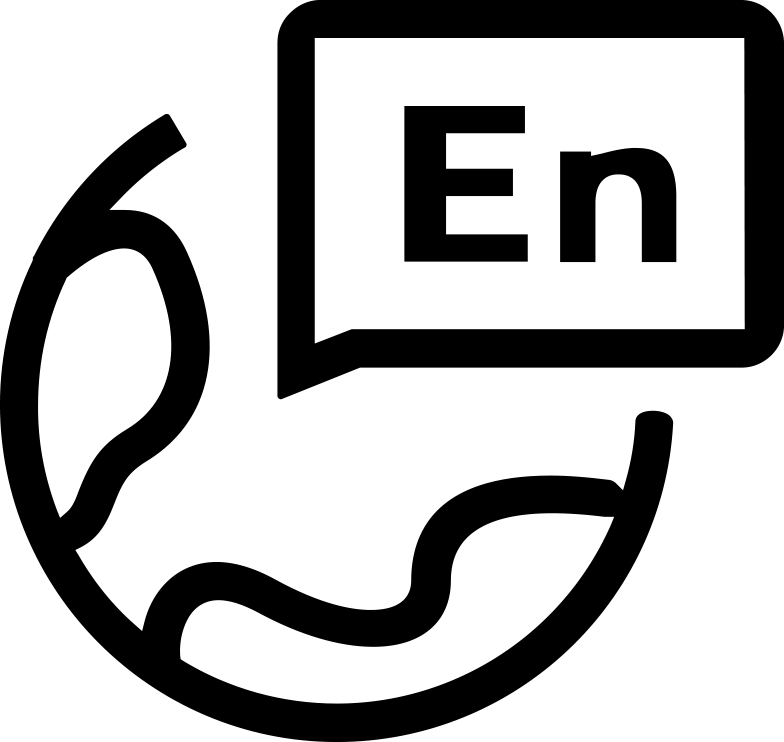在我看来,有三种“恶”无法容忍,分别是:
作恶,即有意识的实施危害他人、社会的恶行;
纵恶,即对作恶者的恶行予以粉饰、纵容及包庇;
助恶,即对反抗恶行的救济行为予以不当打压,助恶为虐,如电影《第二十条》揭露的公民正当防卫权遭遇否定和剥夺,抑或对被害者及其亲友进行人身攻击及否定评价,通过对被害方的苛责来模糊作恶者的责任。
近日,一起未成年人被害案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据公开媒体报道,2024年3月10日,邯郸市肥乡区初一学生王某某被杀害。案件发生后,肥乡区公安机关立即开展侦破工作。3月11日,涉案犯罪嫌疑人被全部抓获,现已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此前,央广网披露,该案3名嫌疑人系被害人的同学,也就是说,嫌疑人的年龄可能在12至14周岁之间,属于我国刑法第17条3款规定的情形。
《刑法》第17条3款规定:已满十二周岁不满十四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该案之所以广受关注,主要是因为涉案人员的年龄与作案手法的残忍程度形成了极大反差,人们在对逝者扼腕叹息的同时,也对涉案人员的心理和行为惊诧莫名。
这些复杂情感背后的拷问在于,对于未成年人的刑事可罚性问题,即为何要对未成年人追究刑事责任,以及应当对其施以怎样的刑罚。
对此,我们不妨将刑法规定与社会生活经验予以结合来作相应探讨。
我国刑法分则规定了400多项罪名,但针对未成年人(特别是年龄在12至14周岁的未成年人),刑法仅将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作为对其应予追责的罪名,并在情节、后果及追诉程序上加以严格限定。
我认为,刑法如此规定的原因大致如下:
第一,相关未成年人对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行为具有辨认、控制能力;
第二,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均是相关未成年人犯罪行为法益侵害的集中体现;
第三,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核准追诉是对相关行为涉嫌犯罪的权威评价。
由此,犯意、法益侵害、权威评价共同构筑了对12至14周岁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追责“门槛”。
这其中,后两点相对显而易见且容易理解,关键就在于对相关未成年人的犯意判断,即如何从法律和经验上评判相关未成年人对其涉案行为具有明确的“犯意”,也即对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行为的辨认、控制能力。
对此,我们不妨通过以下两个问题进行分析:
问题1
相关未成年人能否认识到其行为会导致剥夺他人生命的后果?
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原因在于,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属于典型的“自然犯”,其侵害的对象是他人的生命和健康,是对生存权利的侵犯和剥夺。
因此,对这两类犯罪行为的认识并不需要借助丰富的社会阅历或者高深的专业知识。
而年满12周岁至14周岁的初中生在接受了6年小学教育及10余年家庭(及社会)教育的情况下,对于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行为显然具有认识能力,完全能够认识到相关行为会导致剥夺他人生命的后果。
问题2
相关未成年人是否在追求或放任他人死亡的结果发生?
答案仍然是肯定的。我们常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相信任何具有生之欲望的人都会对剥夺或者危及生命的行为有所排斥,至少,在相关行为施于己身的时候会予以抗拒甚至是反抗。
既然能够清楚的认识到生命之于自身的重要和宝贵,显然也能够认识到他人对于生命的珍视及对生存的渴望。
因此,对自我生命的保护往往出于求生本能,而对他人生命的剥夺及危害则出于杀生的恶意。这种有意识的行为背后所体现的就是行为人主观方面的意识因素,即对相关行为后果的追求或放任。
对年满12周岁至14周岁的初中生而言,生理发育使其具备了剥夺他人生命的身体力量;基于社会、家庭、学校教育所形成的认知能力则决定了其在是否剥夺他人生命的选择上,对其身体力量具有意志支配下的可控性。
综上,在明确12至14周岁未成年人对于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行为具有辨认和控制能力的情况下,对其进行刑事追责显然符合刑法规定刑事责任年龄的应有之义。
行文至此,我们集中对“作恶”进行了探讨和分析,接下来,我们再聊一聊“纵恶”。
任何行为的持续和加强几乎都源于该行为得到的正向反馈,否则,相关行为就会被行为主体予以抑制或放弃。
例如,舔舐糖果令人愉悦,人们会为此不断摄入更多的糖分,而触碰滚烫的汤锅会让人痛苦,所以人们往往会采取种种措施避免对汤锅的触碰。
如前所述,任何具有生之欲望的人都会对剥夺或者危及生命的行为有所排斥,这种排斥既来自于求生的生物本能,也掺杂着物伤其类的人性情感。
因此,对于施暴者而言,其施暴行为的持续发生及加强(乃至达到剥夺他人生命的程度),无疑意味着其在施暴行为中所得到的正向反馈已经远远超出了生物本能和人性情感。
除去因特殊犯罪心理所产生的精神愉悦及因犯罪所获取的物质回报外,施暴行为能够逃避应有的惩罚往往也是刺激该等行为不断持续、加强的重要原因。
在因校园霸凌引发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犯罪中,在长期缺乏有效监管、惩罚的情况下,相关暴行的发生频率及暴力程度往往处于一种持续升级的状态之中,直至发展为剥夺或危及被害者的健康和生命。
据公开媒体报道,在本起邯郸初中生杀人案发生前,被害人疑似长期遭受来自嫌疑人一方的霸凌,并曾向家人作出过不想上学的意思表示。但遗憾的是,我们至今未见有关校方有效处理霸凌的报道。
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本次刑案的发生不仅源于嫌疑人的犯意及罪行,同时也可能源于有关单位对霸凌行为的长期放任和纵容。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9条规定:
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
学校对学生欺凌行为应当立即制止,通知实施欺凌和被欺凌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参与欺凌行为的认定和处理;对相关未成年学生及时给予心理辅导、教育和引导;对相关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给予必要的家庭教育指导。
对实施欺凌的未成年学生,学校应当根据欺凌行为的性质和程度,依法加强管教。对严重的欺凌行为,学校不得隐瞒,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教育行政部门报告,并配合相关部门依法处理。
据此,针对霸凌行为的防控及处理,《未成年人保护法》作出了相对明确、具体的规定,但在实践中,学校是否对此落实到位,恐怕又是一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争论了。
最后,我们再谈一谈“助恶”,以及相关未成年人犯罪可能面临的刑罚。
公众对热点案件的关注必然伴随着争议,其中,对被害者的过分苛责及对施暴者的莫名共情往往屡见不鲜,如“马加爵案”和“药家鑫案”。
此外,实践中的结果定案及客观归罪往往也会模糊施暴者与被害者的界限,如“邓玉娇案”。
即便是在全社会的关注下,这名反抗暴力性侵的女性最终也仅仅得到了“定罪免处”的裁判结果,而非某些媒体宣扬的“无罪释放”。
由此,对被害人而言,在求助遭遇无视,反抗遭受惩罚,甚至在受害都要经受苛责的环境下,其对生命安全的希望仿佛只能寄托于施暴者的“怜悯”和“恩典”。
很多时候,我们会惊诧于被害人在遇害前对施暴者的“顺从”,但我们或许没有意识到,在生命走向终点之前,被害人早已被逼入孤立无援的“孤岛”境地。
尽管刑法的功能不止于“报应”,但事实上,唯一能够告慰死者及安抚生者的,唯有对犯罪者的严惩。
而遗憾的是,我国刑法对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人在量刑上给予了“极大”的“宽容”。
《刑法》第17条4款:对依照前三款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的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刑法》第49条1款: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
据此,本起邯郸初中生杀人案中,如果相关未成年嫌疑人经审理被认定构成犯罪,则他们不仅不会被判处死刑,甚至可能不会被判处无期徒刑。
但需强调的是,根据现行司法解释的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仍存在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情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未成年人犯罪只有罪行极其严重的,才可以适用无期徒刑。对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一般不判处无期徒刑。
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尚未就“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犯罪的情形作出对应的司法解释,但参照上述解释内容,相关嫌疑人仍存在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现实可能。
当然,对未成年人犯罪不能一判了之,更应严惩纵恶助恶责任链条上的相关人员。我们关注本案的后续进展及处理结果,更希望本案所引发的关注和讨论能够转化为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有效治理和积极预防。
最后,希望我们和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越来越美好。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