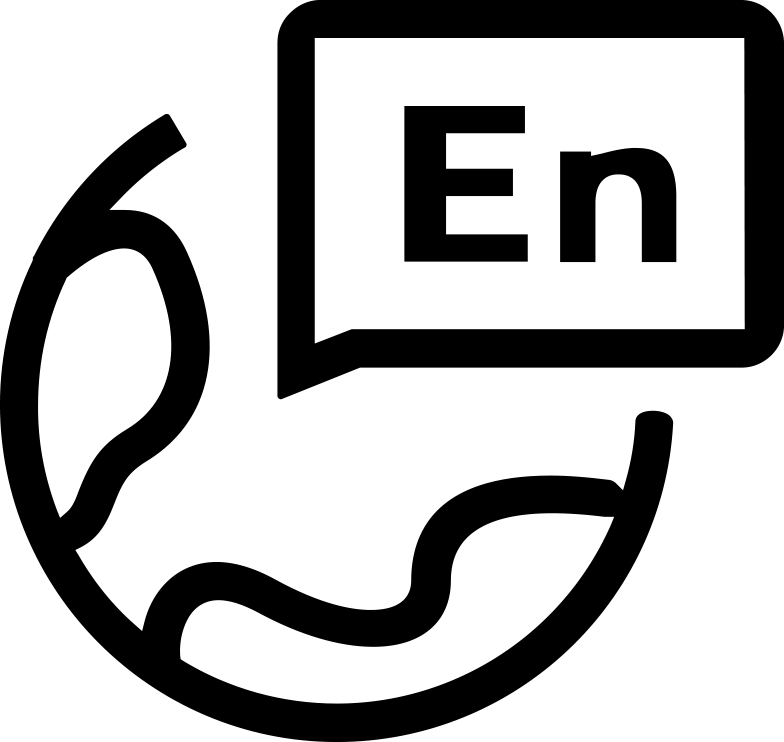近年来,我国证券、期货市场发展迅速,国家对其监管力度也逐渐加大,但在巨额利益驱使下,证券、期货市场犯罪频发,屡禁不止。2020年3月1日开始实施的《证券法》扩大了内幕信息知情人员的范围,细化了对内幕交易的认定,大幅提升了内幕交易的惩处力度。内幕交易罪是证券市场上常见的犯罪类型,该罪侵犯了公众投资者的平等知情权和财产权益,对证券市场的合法运行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严重侵害国家对证券、期货市场的管理秩序,严重阻碍了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2024年4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制定了《关于办理证券期货违法犯罪案件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坚持依法从严惩处,充分发挥刑罚的惩治和预防功能,严格控制不起诉、免于刑事处罚、缓刑的适用。证券违法犯罪迎来了空前的执法力度,“零容忍”“从严从快”的执法态势让资本市场的“暗流”无处遁形。在此背景下,笔者结合自身办理内幕交易案件的经验,谈谈内幕交易罪在司法实务中的认定标准和刑事辩护路径,以期为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中的规范交易、合规运行明确刑事法律红线。
一、实践中关于内幕交易罪的常见情形
内幕交易犯罪被称为“资本市场的老千”,是证券市场中典型的利用信息优势获取不当利益的投机行为,内幕交易罪的客观行为就是相关交易行为,2012年3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内幕交易司法解释》),根据该解释,结合司法实践,内幕交易罪中的“相关交易行为”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形:
(一)内幕信息知情人员从事的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证券、期货交易
在宋某军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案【(2017)鲁05刑初3号】中,被告人宋某军作为案涉公司“和力投资”的法人及股东,股权占比34%,“吉艾科技”又是“和力投资”的控股股东,股权占比51%,2015年,马某岳作为“和力投资”股东,了解到哈萨克斯坦多斯托克炼油厂的情况,并建议吉艾科技收购该炼油厂以解决中塔石油的原油采购问题。马某岳向郭某祥和宋新军汇报了相关情况,并在宋新军的指导下准备了谈判注意事项。2015年7月20日至8月5日,宋新军安排季某使用宋新军的证券账户,在吉艾科技筹划收购哈萨克斯坦炼化企业的内幕信息公开前,大量买入吉艾科技股票,共买入股票1648520股,成交金额达22853030.95元。2015年10月12日,吉艾科技股票复牌,宋新军指示季某卖出部分股票,当日所持股票盈利5066388.77元。
本案中,被告人宋新军作为知悉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其交易行为发生在吉艾科技公告筹划收购事项前后,被告人在上市公司筹划重大投资行为的信息公开披露前利用该信息从事相关交易,且交易量和盈利显著,法院经审判,最终认定被告人宋某军的行为构成内幕交易罪。
又如在徐某庭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案【(2015)粤高法刑二终字第134号】中,2011年10月,深圳广电集团计划将天宝公司和天隆公司的网络资产和业务注入天威视讯,该信息被认定为内幕信息,敏感期为2011年10月18日至2012年6月11日。天宝公司副总经理徐德庭作为知情人员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进行了天威视讯股票的交易,多次买卖天威视讯股票,累计买入113500股,成交金额1889346元,卖出相同股数,盈利32016.88元。
本案中,被告徐德庭作为深圳市天威视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在对天威视讯公司资产、负债等产生重要影响的合同订立的信息公开披露前利用该信息从事相关交易,交易量和盈利显著,法院最终认定其行为构成内幕交易罪。
又如杜某库等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案【(2011)锡刑二初字第0002号】被告人杜兰库担任中国某集团公司(某集团)的总会计师,负责重大投资事项。2009年3月23日,杜兰库在南京听取了下属研究所(某所)关于通过收购上市公司方式借壳上市的汇报,从而掌握了关键的内幕信息,即某所拟收购、重组的目标公司为江苏某股份有限公司(某公司)。杜兰库知悉的信息是能够对某公司证券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内幕信息,且该信息在听取汇报时尚未对公众公开。杜兰库将该重组信息告知了被告人刘乃华。杜兰库与刘乃华合谋,在内幕信息公开前,利用本人及他人的证券交易账户进行交易。两人在敏感期内买卖某公司股票共计36万股,非法获利共计4,210,043.84元。其中,杜兰库单独操作获利2,470,351.38元,杜兰库与刘乃华共同操作获利1,739,692.46元。
本案中,被告人杜兰库作为某集团总会计师参与某所与某公司资产重组事项,因履行工作职责获取了内幕信息,系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被告人刘乃华从配偶杜兰库处获悉上述内幕信息,系非法获取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在内幕信息尚未公开前,被告人杜兰库、刘乃华共同利用该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被告人刘乃华还将内幕信息泄露给他人。法院依法认定被告人杜兰库的行为构成内幕交易罪,被告人刘乃华的行为构成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
(二)被明示、暗示的人员从事的与内幕信息有关的证券、期货交易
在林某2、苏某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案【(2021)湘0103刑初24号】中,2014年底,中介机构向华贸物流推荐中特物流有限公司(中特物流)开展重组业务。2015年1月31日,林红陪同中特物流董事戴东润等人考察华贸物流。之后,双方就重组事宜进行了多次沟通。2015年3月20日,双方在北京北大博雅国际酒店举行见面会,明确表示重组意愿并达成初步意向。2015年7月21日,华贸物流发布股票停牌公告。停牌期间,发布了关于收购中特物流的相关公告。林红作为中特物流财务总监,参与了重组事项,是内幕信息知情人。林红在敏感期内向苏艳芝泄露了中特物流并购重组的内幕消息。苏艳芝利用内幕信息,使用本人及“谭某斯”账户买入华贸物流股票,成交金额263万余元,复牌后卖出,亏损16万余元。
本案中,被告人林红是内幕信息知情人,林红将相关内幕信息在敏感期内泄露给苏艳芝,明示苏艳芝进行相关的股票交易,情节特别严重,林红的行为构成泄露内幕信息罪,苏艳芝的行为构成内幕交易罪。
又如汪某某等泄露内幕信息、内幕交易案【(2016)沪刑终141号】世纪鼎利公司是一家上市公司,上海智翔信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上海智翔公司)是一家成立于2006年的公司。汪某某自2013年1月16日起担任上海智翔公司的副总经理。2014年3月,世纪鼎利公司与上海智翔公司就并购重组进行了多轮磋商,并最终达成共识。2014年5月30日,世纪鼎利公司股票停牌,并于7月29日发布收购上海智翔公司100%股权的公告,7月30日股票复牌。汪某某作为上海智翔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在4月底获悉了世纪鼎利公司可能收购上海智翔的内幕信息。汪某某在5月2日与姐夫彭强见面时谈及世纪鼎利公司情况,并在5月28日向彭强拨打电话。汪某某在5月3日与岳母项某某见面时告知了世纪鼎利公司可能的重组信息。彭强根据汪某某的信息,指示妻子孙某某抛售原有股票后全仓买入世纪鼎利股票20万余股,成交金额361万余元,并在微信群推荐该股票,后卖出获利27万余元。项某某根据汪某某的信息买入世纪鼎利股票,并在停牌前后卖出,获利24万余元。
本案中,被告人汪某某作为上海智翔公司的副总经理,依照相关规定属于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在上海智翔公司与世纪鼎利公司并购重组内幕信息的敏感期间内,汪某某将工作中获取内幕信息告诉被告人项某某、彭强,导致项某某、彭强从事“世纪鼎利”证券交易成交额为468万余元,获利数额为52万余元,法院认定其行为已构成泄露内幕信息罪,被告人彭强、项某某并非内幕信息的法定知情人员,在从被告人汪某某处非法获取相关内幕信息后,进行“世纪鼎利”股票交易,交易额分别为361万余元、107万元,非法获利分别为27万余元、24万余元,行为均已构成内幕交易罪。
(三)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从事的与内幕信息有关的证券、期货交易
在陈某红等泄露内幕信息、内幕交易案【(2015)沪高刑终字第140号】中,另一被告人刘某因投资“晟纳吉公司”与“天龙光电公司”的陈必红等人不定期见面,刘某从陈必红处获悉天龙光电将出售单晶炉和研发蓝宝石屏幕样品取得进展的内幕信息,以及用租金抵偿债务的方案。2013年9月11日至13日,刘某指使洪某利用控制的证券账户买入天龙光电股票31万余股。2013年9月25日,刘某卖出部分天龙光电股票。2013年11月1日,刘某通过洪某持续交易天龙光电股票,最终持有246万余股。2013年11月6日,刘某指使洪某抛出所持有的全部天龙光电股票,共计购入319万余股,总成交金额2336万余元,获利139万余元。
法院认为,被告人陈必红作为涉案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在敏感期内将涉案内幕信息告诉被告人刘某等人,导致刘某进行天龙光电证券交易,其行为已构成泄露内幕信息罪。刘某并非涉案内幕信息的法定知情人,在从陈必红处非法获悉涉案内幕信息后,指使他人利用实际控制的证券帐户进行天龙光电证券交易,其行为已构成内幕交易罪。
又如陈海啸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2020)皖刑终16号】案中,2013年11月,东源电器第一大股东孙某1委托金通智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处理股份减持及重组事宜。薛某1作为金通智汇负责人,参与重组事宜,成为内幕信息知情人。2013年11月中旬,陈海啸咨询薛某1相关股权转让事项。2013年11月18日至2014年1月24日,陈海啸使用本人证券账户买入东源电器股票247.843万股,成交金额1628.07455万元。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薛某1安排朱某借给陈海啸3100万元,陈海啸用该笔资金购买东源电器股票。陈海啸通过质押东源电器股票融资2200.147万元,继续购买股票。2013年11月18日至2014年3月31日,陈海啸共买入东源电器股票1022.1469万股,成交金额6919.690825万元。股票停牌与复牌:2014年4月1日,东源电器股票停牌;9月10日公告重大资产重组信息并复牌。2014年9月19日和24日,陈海啸将所持东源电器股票全部卖出,获利10381.658135万元。
根据《内幕交易司法解释》,非法获取证券内幕信息的人员包括非法手段型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特定身份型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和积极联系型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三类人员。其中特定身份型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是指内幕信息知情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关系密切的人员(包括基于学习、工作产生的关系,如同学、校友),这类人员无论是主动获取还是被动获取内幕信息,均属于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本案中,薛某1属于“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其他人"。根据在案证据,薛某1介绍了东源电器与余某1的资产重组、借壳上市以及与国轩高科的资产重组,巢东股份与顾家家居、新力投资的重组事宜,薛某1基于中间人、介绍人的身份全程参与重组过程,属于法定内幕信息知情人,陈海啸从薛某1处既有被动获取也有主动获取内幕信息的行为,系非法获取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其在内幕信息尚未公开前,从事与内幕信息有关的股票交易,成交额9592.715906万元、获利1.0381658135亿元,法院依法认定其构成内幕交易罪。
再如满某某、孙某甲泄露内幕信息、内幕交易案【(2016)鲁05刑初14号】,2013年9月,宝莫股份总经理刘某皓与康贝石油董事长满某某达成合作投资加拿大锐利能源的口头意向。2013年10月-11月,满某某与刘某皓在加拿大与锐利能源达成三方初步合作意向框架协议。宝莫股份于2013年12月9日发布停牌公告,2014年1月19日董事会审议通过收购康贝油气工程有限公司和锐利能源股权的议案,1月21日公告公开披露,股票复牌。满某某作为知情人员,在敏感期内将内幕信息泄露给孙某甲、宋某燕、刘某芬、王某霞等人。孙某甲使用杨某霞账户为满某某等人交易宝莫股份股票,买入804010股,成交金额670.29万元,卖出后盈利126.04万元。王某霞使用自己账户买入2100股,成交金额1.58万元。孙某甲使用自己账户买入164600股,成交金额133.64万元,卖出后盈利35.73万元。
本案中,被告人满某某作为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在涉及证券交易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尚未公开前,泄露该信息明示、暗示他人交易该证券,安排孙某甲为其买入或卖出该证券;被告人孙某甲作为非法获取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在涉及证券交易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尚未公开前,买入该证券,同时按照被告人满某某的安排及他人的委托实施该证券的交易行为。法院认定被告人满某某作为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向他人泄露内幕信息,委托他人从事买入或卖出该证券的交易活动、系主犯,构成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被告人孙某甲虽系交易活动的直接实施者,但泄露、交易行为均受满某某的指挥,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应认定为从犯,构成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
还如倪某某、胡某某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案【(2015)粤高法刑二终字第151号】,2011年10月,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计划改革重组,包括天宝公司和天隆公司并入天威视讯,该信息被认定为内幕信息,敏感期为2011年10月18日至2012年6月11日。被告人倪鹤琴作为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敏感期内泄露信息给曾云发和胡宁和。倪鹤琴于2012年1月19日使用自己账户购买天威视讯股票30000股,交易金额446400元。倪鹤琴将140万元资金转至曾云发账户,并指令其购买天威视讯股票,曾云发在指定期间共交易股票109200股,交易金额1784516元。胡宁和在获取内幕信息后,通过控制他人账户共交易天威视讯股票18xxx25股,交易金额31681774.78元。魏薇从曾云发处获取内幕信息,于2013年2月13日至3月1日通过本人账户交易天威视讯股票58000股,交易金额975520元。
本案中,被告人倪鹤琴作为内幕信息知情人,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使用自己的证券账户交易天威视讯股票,并通过曾云发代理交易天威视讯股票,以及向被告人胡宁和、曾云发泄露内幕信息,导致后者从事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证券交易,情节特别严重,法院认定其行为已构成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被告人胡宁和从被告人倪鹤琴处非法获取证券交易内幕信息,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交易天威视讯股票,情节特别严重,法院认定其行为已构成内幕交易罪。被告人曾云发从被告人倪鹤琴处非法获取内幕信息后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交易天威视讯股票,并向被告人魏薇泄露该内幕信息,导致后者从事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证券交易,法院认定其行为已构成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被告人魏薇从被告人曾云发处非法获取证券交易内幕信息,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交易天威视讯股票,情节严重,法院认定其行为构成内幕交易罪。
当然,实务中的内幕交易犯罪情形复杂、多样,本文篇幅有限难以全部介绍。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内幕交易行为不仅涉及直接的交易者,还可能牵扯到一系列复杂的市场参与者,包括但不限于公司高管、内部员工,甚至是与知情人有密切联系的第三方。这些个体可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或参与了内幕信息的获取、泄露或交易过程。
二、“内幕交易罪”在实践中的认定
针对当前国家对证券期货违法犯罪坚持的零容忍、严监管的政策导向,结合刑事司法审判中的实务案例,笔者围绕知情人员、内幕信息、内幕信息敏感期、非法获取内幕信息人员、交易行为明显异常、哪些行为不构成内幕交易这几个关键要点,从司法实务中对内幕交易行为的认定思路出发,浅析“内幕交易罪”在实践中的认定。
(一)知情人员的界定
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包括基于管理地位、监督地位、职业地位或者通过职务行为能够接触或者获得内幕信息的人员。新《证券法》第五十一条对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做出界定,根据该规定,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包括:
(一)发行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二)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三)发行人控股或者实际控制的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四)由于所任公司职务或者因与公司业务往来可以获取公司有关内幕信息的人员;
(五)上市公司收购人或者重大资产交易方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六)因职务、工作可以获取内幕信息的证券交易场所、证券公司、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服务机构的有关人员
(七)因职责、工作可以获取内幕信息的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工作人员;
(八)因法定职责对证券的发行、交易或者对上市公司及其收购、重大资产交易进行管理可以获取内幕信息的有关主管部门、监管机构的工作人员;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的可以获取内幕信息的其他人员。
新《证券法》几乎将知悉或能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都纳入到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为后续全面和精准打击内幕交易提供了法律依据。2024年《意见》也指出,对“关键少数”,如证券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金融从业人员等,实施证券违法犯罪的,应当依法从严惩处。
需要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刘宝春、陈巧玲内幕交易案的裁判要旨明确,国家工作人员因履行工作职责而获取对证券交易价格具有重大影响的、尚未公开的信息的,也属于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
(二)内幕信息的界定
在某种意义上,证券市场就是信息市场,证券市场中各种信息是投资者投资决策的基本依据。虽然市场充斥了各种各样的信息,但是并非所有的信息都会影响证券价格,准确认定内幕信息,是认定内幕交易罪的重要前提。内幕交易犯罪作为行政犯,由刑法规定该罪名的主客观要件,而具体的行为内容则由行政法律法规予以认定。刑事处罚是对内幕交易犯罪行为的规制,而行政处罚是对内幕交易违法违规行为的规制。根据《证券法》第52条、第80条、81条对内幕信息的规定,构成行政法律法规和刑事法律层面的内幕信息,应当满足“秘密性”“重大性”和“关联性”三个特征。
首先,“秘密性”是指信息“尚未公开”,仍由少部分内部人员掌握,尚未被证券、期货投资者所知悉。行为人基于已公开的信息进行交易的,通常不构成内幕交易。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信息是否公开是正确认定内幕交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从司法实务的惯行标准来看,认定内幕信息公开的三个要件,第一,相关媒体报道能够为市场主体所广泛周知;第二,媒体所揭露的信息具有完整性,即已经包含内幕信息的主要内容,从而使理性的市场主体能够就其可能产生的市场影响进行综合判断;第三,理性的市场主体能够相信相关媒体揭露的信息具有可靠性。
在杨剑波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诉讼案件中,行为人主张错单交易信息在案发当日下午对冲交易开始之前,已经被媒体揭露从而处于公开状态,不构成内幕信息。但最终法院认定,原告所主张的相关网络媒体关于错单交易信息的报道对市场主体来说不能满足可靠性的要求:首先,原告所举某世纪网的报道中并未准确指明其报道的信息来源,市场主体无法确信该报道来自于可靠的信息源;其次,原告提交的其他网站对于错单交易信息的报道均是对某世纪网报道的转载,并非基于各自独立调查而进行的报道,不能形成相互佐证的关系从而使市场主体相信其内容真实可靠;最后,在某证券公司于当日下午发布公告之前,相关媒体对当日上午大盘指数大幅上涨的原因还有诸多其他推测和报道,市场主体无法仅仅基于某世纪网的报道而相信其内容真实可靠。因此,原告主张错单交易信息在某证券公司当日下午对冲交易开始之前已经公开的主张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由此可见,就算相关信息已经被媒体披露,但只要市场主体未依据该信息做出相关反应,法院会认为市场主体不会相信其内容真实可靠,不符合公开标准,将其认定为尚未公开。
其次,“重大性”是指信息“对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有重大影响”。在“有重大影响”的判定上,国务院《期货交易管理条例》《证券法》《刑法》都将“重大性”作为认定内幕信息的要件,但三者所表述的“重大性”有着本质区别。《期货交易管理条例》使用“可能对期货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之表述,证券法采用“对该公司证券的市场价格有重大影响”之表述,刑法则表述为“对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有重大影响”。“可能有”重大影响是内幕交易违法行为的要件,而“有”重大影响才是内幕交易犯罪行为的要件。如果行为人利用某信息进行证券、期货交易,但事实上该信息未对证券、期货价格有重大影响的,就不能构成犯罪,而只能以违法行为论处。重大性是判断是否够构成内幕交易的核心标准之一,也是实践中判断的重点。
最后,“关联性”是指内幕信息是与发行人本身密切相关的财务或者经营方面的信息。关联性是区分内幕信息与其他未公开的市场信息的关键,通常认为,在证券期货市场中因投资者的交易行为直接产生的相关交易信息,因为该信息和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不直接相关,因此不属于内幕信息。对与利用此类不属于内幕交易的未公开信息进行交易的,因为此种交易会损害市场公平性,《刑法修正案(七)》单独设置了“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以追究利用内幕信息以外的未公开信息进行交易的行为。但是,如果该交易信息与发行人或者上市公司直接相关,比如说涉及发行人的某项对外投资收购计划、重大改革重组,一经公布会对发行人的股票、债券的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就属于内幕信息。
(三)内幕信息敏感期的界定
内幕交易敏感期在认定内幕交易罪的过程中同样十分重要,敏感期的认定关乎相关信息能否被认定为内幕信息,以及确认内幕信息法定知情人范围、行为人违法所得的计算。《内幕交易司法解释》第五条规定,本解释所称“内幕信息敏感期”是指内幕信息自形成至公开的期间。因此,认定内幕信息敏感期涉及两个关键时间节点:一是内幕信息形成时,二是内幕信息公开时。具体而言:
1.内幕信息形成时
根据《内幕交易司法解释》第五条第二款和第三款进一步规定,“重大事件”的发生时间、相关“计划”、“方案”、“政策”、“决定”等形成时间,应当认定为内幕信息的形成之时,影响内幕信息形成的动议、筹划、决策或者执行人员,其动议、筹划、决策或者执行初始时间,应当认定为内幕信息的形成之时。
实践中,经常被认定为内幕信息形成之日的情形有提出方案之日【如(2015)沪高刑终字第140号、(2017)浙01刑初28号判决】、合作框架初步形成之日【如(2011)锡刑二初字第0002号判决】、双方谈判后就合作内容基本达成一致意见之日(如罗高峰等内幕交易案)、召开上市工作准备会之日【如(2019)京02刑初141号判决】、开始重组考察之日【如(2021)湘0103刑初24号判决】、签订保密协议等文书之日【如(2020)4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主管机关领导知情之日【如(2015)粤高法刑二终字第151号判决】等。
2.内幕信息公开时点
《内幕交易司法解释》第五条第四款规定,内幕信息的公开是指内幕信息在国务院证券、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指定的报刊、网站等媒体披露。实践中,对于媒体率先披露内幕信息的情况,在上市公司或者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未披露的情况下,上市公司或者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应立即予以澄清。在证监会指定媒体正式公告之前,知悉内幕信息的人不应进行交易,其他投资者可以进行交易。对这些投资者来说,媒体的率先报道通常被视为市场传言。信息披露义务人公开披露内幕信息的媒体也是有特殊要求的,对于普通网站和报纸而言,人们未必信赖,相关信息的真实性无法保障。为了规范性、权威性,法律将内幕信息公开的形式做了特殊规定,例如中证网、中国证券网、证券时报网等指定媒体。
同时,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证监会对内幕信息敏感期的认定并不是都被法院在刑事审判程序中采纳,实践中还有法院认定的内幕信息敏感期的起始点早于证监会认定的起始点的情况。例如在陈某某内幕交易案【(2015)沪高刑终字第140号】中,证监会的调查报告和司法鉴定意见将内幕信息形成时间点认定为2013年9月5日。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上述信息是上海超日董事长倪某某在2013年8月提出,双方于2013年9月5日达成合意,并且主张司法机关对于证券违法犯罪行为应当具有独立判断的权力,对调查报告和鉴定意见中的客观内容予以采纳并进行独立的刑事认定符合法律规定,故应当将8月视为本案内幕信息敏感期的起点。
(四)非法获取内幕信息人员的界定
内幕交易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包括两类人员,内幕信息的法定知情人员和非法获取内幕信息人员。如前所述,内幕信息的法定知情人员以及由法律、行政法规所规定,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也是内幕交易罪的重要行为人,对于非法获取内幕信息人员的认定,要求行为人主观上根据信息内容与价值,能够认识到其获取的信息是内幕信息,根据该内幕信息的来源和传播途径,能够认识到内幕信息直接或者间接来源于内幕信息知情人。根据《内幕交易司法解释》第二条规定,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概括起来包括三类:
第一,非法手段型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即获取信息的手段行为本身是非法的,如通过窃取、骗取、套取、利诱、刺探手段获取内幕信息的。此类人员属于典型的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特点在于其获取内幕信息的手段上具有非法性和主动性。
如在张某2内幕交易案【(2017)浙01刑初28号】中,张某与王某接触过程中获悉东某公司近期有资产重组安排,后为非法获取该内幕信息,向王某打探并确认东某公司即将收购某威克公司的信息并进行内幕交易,最终被法院认定其通过刺探方式非法获取内幕信息,构成内幕交易罪。
第二,特定身份型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即获取信息的手段行为未必是非法的,但其作为特定身份的人员不应获取内幕信息,如内幕信息知情人员的配偶从知情人员处获取内幕信息等。此类人员主要是基于内幕信息知情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关系密切的人这种特殊身份,且必须满足相关交易行为明显异常,无正当理由或者正当信息来源等限定条件。
如在李某2等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案【(2019)京02刑初141号】中,王某某是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李某2为取得李某、杨某之女法律上的抚养权,与王某某商量后登记离婚。此后,王某某在李某2交易某电力股票前后,多次为李某2归还信用卡,二人还以夫妻名义参加同事聚会,共同探亲、出行旅游,王某某以母亲身份帮忙照顾孩子。李某2与王某某虽登记离婚,但在经济、生活上仍保持密切联系,法院将李某2认定为与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关系密切的人员。
第三,积极联系型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即主动联络、接触的行为未必是非法的,但结合行为目的分析,行为人是从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处获取不应该获取的内幕信息,因此获取行为是非法的。此类人员常见于同学、战友、下属、朋友、合作伙伴等关系,且必须满足交易行为明显异常、无正当理由或者信息来源等限定条件。
例如在北京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李某某内幕交易案【(2023)京03刑初24号】中,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公司与上述内幕信息的参与者A数据集团有限公司之间具有多项业务合作,并签订多份合作协议,其中两份协议书由被告人李某某与王某某代表各方签署。李某某在敏感期内曾收藏来自王某某的微信信息,并且李某某、王某某和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陈某某三人曾因合作事项面谈。法院认为,综合在案证据可以判定,李某某与内幕信息知情人王某某有联络、接触行为。在内幕信息敏感期内,被告李某某与内幕信息知情人员联络、接触,从事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证券交易,相关交易行为明显异常,且无正当理由或者正当信息来源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一款规定的“非法获取证券内幕信息的人员”。
此外,实践中对被动型获悉内幕信息的人员是否也纳入责罚范围有较大争议,《内幕交易司法解释》暂时并没有将被动型获悉内幕信息的人员明确规定为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以下简称《<解释>理解与适用》)中提到,“出于审慎起见,刑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并未将被动型内幕信息人员纳入本罪的法定主体范围”。
但是实践中也存在惩处被动型获悉内幕信息的人员,如(2019)粤03刑初473号一案中,行为人是以被动方式(听到朋友打电话)来获取到内幕信息的,但法院最终还是判定该行为人构成内幕交易罪,表明了监管机关和司法机关惩处内幕交易的决心。
(五)交易行为明显异常的界定
“交易行为明显异常”是一种定性加定量的模式,对“交易行为明显异常”的判断类似于防卫过当中对“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的判断,“异常”是一种定性,而“明显”是一种定量。根据《内幕交易司法解释》第三条规定,“相关交易行为明显异常”,要综合以下情形,从时间吻合程度、交易背离程度和利益关联程度等方面予以认定:
(一)开户、销户、激活资金账户或者指定交易(托管)、撤销指定交易(转托管)的时间与该内幕信息形成、变化、公开时间基本一致的;
(二)资金变化与该内幕信息形成、变化、公开时间基本一致的;
(三)买入或者卖出与内幕信息有关的证券、期货合约时间与内幕信息的形成、变化和公开时间基本一致的;
(四)买入或者卖出与内幕信息有关的证券、期货合约时间与获悉内幕信息的时间基本一致的;
(五)买入或者卖出证券、期货合约行为明显与平时交易习惯不同的;
(六)买入或者卖出证券、期货合约行为,或者集中持有证券、期货合约行为与该证券、期货公开信息反映的基本面明显背离的;
(七)账户交易资金进出与该内幕信息知情人员或者非法获取人员有关联或者利害关系的;
(八)其他交易行为明显异常情形。
时间吻合程度,即从行为人开户、相关交易、资金变化等时间与内幕信息形成、变化、公开的时间吻合程度上把握;交易背离程度,即从交易行为与正常交易的背离程度上把握,正常交易主要体现为基于平时交易习惯而采取的相似交易行为,或基于证券、期货公开信息反映的基本面而在合理预期之内进行的交易行为;利益关联程度,即从账户交易资金进出与该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或者非法获取人员有无关联或者利害关系把握。法条中的综合把握,是指不能单纯从上述某一个方面认定交易是否明显异常,而必须综合三个方面进行全面分析、论证。而考虑到实际案件情况往往错综复杂,许多情形难以预料,《内幕交易司法解释》第三条第八项还规定了兜底项。实践中,对于内幕交易中的交易行为明显异常的认定,可借鉴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第65号指导案例“王鹏等人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案。该案的案例要旨在于,被告人王鹏作为具有获取未公开信息职务便利条件的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其本人及其近亲属从事相关证券交易行为明显异常,且与未公开信息相关交易高度趋同,即使其拒不供述未公开信息传递过程等犯罪事实,但其他证据之间相互印证,能够形成证明利用未公开信息犯罪的完整证明体系,足以排除其他可能的,可以依法认定犯罪事实。
同时目前很多案件中,有些行为人会以自己长期交易习惯、风格如此、交易行为是其独立判断作为对交易行为明显异常的抗辩,如,在林平忠等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2017)闽刑终43号】案中,林平忠及其辩护人辩称,“林平忠作为一个专业股票分析师、资深炒股人员及大学证券投资课程教师,长期关注并从事重组题材股票交易,多次准确判断宝诚股份、ST成霖、ST白猫等股票停牌重组。其根据银润投资的盈利情况等公开信息,足以判断出银润投资是优质的壳资源,日后必然重组”。该案的承办法官认为,“炒股资金需要成本,持股等待时间的长短与收益密切相关,确定重组的可期待性之后仍要面临何时重组的问题,专业技术水平高不等于可以准确判断何时重组”。
实践中,决定或影响股票交易行为的因素具有多样性,往往是多因一果,专业技术判断与获得内幕信息可以同时影响或促成股票交易。在认定某一股票交易行为是否构成内幕交易时,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获得相关内幕信息并进行了股票交易,而不在于行为人之前对该股票是否看好或证券交易水平的高低。本案中,有充分证据证明林平忠所获取的重组内幕信息,对其交易银润投资股票产生了决定作用,其之前通过自己的专业技术判断银润投资可能重组并不影响内幕交易罪的成立。
三、内幕交易案件的刑事辩护路径
依据当前刑法主流理论,归纳目前公开裁判文书中内幕交易罪辩护意见,结合笔者的实务辩护经验,将实务中内幕交易罪的相关辩护要点总结如下:
(一)主体之辩:不是内幕信息的知情人或者不是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
内幕交易罪是特殊主体犯罪,仅有两种特殊主体可以构成内幕交易罪:一是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二是非法获取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如果行为人并不是因职务、职责等直接获取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也不是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那么辩护方大部分会从犯罪主体方面展开辩护。
实务中辩护人主张无罪辩护的案例中,其中一个重要理由即是被告人主体不适格,如冯方明内幕交易【(2015)粤高法刑二终字第215号】案中,辩护方主张行为人依据已被他人披露的信息而交易,有正当的信息来源,而非内幕信息知情人员。
新《证券法》更侧重于以职务行为为判断依据,即是否因工作需要接触到内幕信息,从而判定是否应负有保密义务,是否划为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在具体处理此类案件时,需要深入分析行为人获取内幕信息的具体情形,考虑其是否因职权或职务行为而接触到这些信息,并严格界定其是否负有保密这些信息的责任,不能简单地因为行为人具有某种职业身份,就默认其为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如果经过评估确定行为人并无保密内幕信息的义务,则不应被归类为内幕信息的知情人。这种情况下,行为人不符合内幕交易罪的主体要求,其行为不应构成犯罪。
(二)客观之辩:交易没有明显异常或者不具有内幕交易行为
当行为人被认定为交易行为异常后,举证责任发生反转,需要由辩方提供证据,证明异常交易行为有正当理由,或者有正当信息来源。对于相关交易行为明显异常,《内幕交易司法解释》第三条则从时间吻合程度、交易背离程度和利益关联程度等方面予以认定,并详细列举了相关异常情形。辩护方可以从该规定列举的异常情形出发进行辩护,如果只是一般异常或者有其他合理的解释,也可以作为辩护要点之一。
如侯某丽、兰某犯内幕交易案【(2017)冀01刑初102号案】中,辩护方主张交易行为确属反常,但无法查明“内幕信息”来源的,不能认定行为人属于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员。法院认为控方提供的证据,不足以排除侯某丽从网络得知“重组、收购”信息的辩解。侯某丽交易行为虽反常,但内幕信息来源不明,认定其非法获取内幕信息并构成内幕交易罪的证据不足,无法认定其构成内幕交易犯罪。
(三)对象之辩:相关信息不构成内幕信息
内幕信息之所以冠以“内幕”,实质是因为其系处于未公开状态下的信息,也即《证券法》52条规定的内幕信息三个特征之一的“秘密性”。在内幕交易刑事案件的辩护中,除了主客体应当重点关注之外,内幕信息是否真正为之“内幕”,是否具有隐秘性,也是必须重点挖掘的辩护要素。
在王某2等泄露内幕信息、内幕交易【(2015)粤高法刑二终字239号】一案中,行为人称在内幕信息(公司即将重组)对外公示前,公司重组的准备和传闻就已经在公司内传播了近3年之久,被告人辩称认为公司重组并不是什么秘密,但法院认为,坊间传闻不是信息公开,相关媒体推测不是信息公开,“在对证券交易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披露前,相关媒体发布的推测性信息及行业内的传闻等均具有不确定性,不能认为是本案内幕信息已经公开”。
在内幕交易类案件中,尤其应当注意信息是否仍为“非公开”状态,我国内幕信息的公开采取“形式公开”的标准。《证券法》第86条规定,“依法披露的信息,应当在证券交易所的网站和符合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条件的媒体发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8条规定,“依法披露的信息,应当在证券交易所的网站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媒体发布”;《内幕交易司法解释》第5条规定,“内幕信息的公开,是指内幕信息在国务院证券、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指定的报刊、网站等媒体披露”。因此,如果是其他人在非特定网站、媒体披露的信息促使行为人从事股票证券交易,即使从非特定网站、媒体获悉的信息与后来证券交易所的网站和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媒体披露的内幕信息相同,行为人也可基于这一事由主张自己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四)交易原因之辩:不是基于内幕信息去交易
鉴于近年来证券、期货市场犯罪的专业化、隐蔽化等特点,司法机关为从严打击证券、期货犯罪,对内幕信息的影响力不作程度限制,不要求内幕信息对行为人交易决定的影响是唯一的,只要行为人获取的内幕信息对促使其交易决定有一定影响,就认定行为人利用内幕信息进行相关交易。
但利用自身知识储备、经验、专业等进行证券、期货交易是司法实践中的常见辩点,如陈某4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案【2015)浙杭刑初字第78号】、石某甲、蔡某甲内幕交易案【(2015)中二法刑二初字第243号】等案例中,此种关于交易原因非内幕信息的获取而是基于自身专业经验,均成为辩护的要点之重。
此外,还应当尝试排除行为人进行交易行为与内幕信息的相关性,审查行为人是否根据内幕信息外的其他理由和依据进行的股票交易,如个人对股票的评价分析、股票网站消息参考等。
(六)量刑之辩
实务中,不少案件中辩护人会围绕被告人是否具有自首、立功、从犯、认罪认罚等法定情节和初犯、退赃、悔罪、没有再犯危险等酌定情节进行辩护,主张从轻、减轻、免除处罚或宣告缓刑,包括罚金刑辩护。
在审查起诉阶段,例如渝检一分院刑不诉〔2019〕9号中,检察机关认为,行为人内幕交易行为,但犯罪情节轻微,案发后行为人主动投案,如实供述罪行,有自首情节,属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在审判阶段,陈跃洪泄露内幕信息一案【(2017)闽刑终43号】,二审法院纠正了自首的认定情节,将一审法院的有期徒刑五年改为一年;金建平、吕悦明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2013)浙刑二终字第135号】案中,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原判认定事实清楚,定性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根据两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及案发后如实交代、清退赃款和有立功表现等,对两被告人还可加大从宽处罚幅度,鉴于两被告人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等情况,判处刑罚可同时适用缓刑。
上诉及辩护要求对两被告人再予从轻处罚及适用缓刑的部分理由成立,予以采纳;茹振刚、张彩娟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一案【(2019)粤刑终1221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二审中,茹振刚自愿认罪并出具了认罪书,兼顾考虑其归案后能稳定供述交易过程,依法可予以从轻处罚。
内幕交易类刑事案件中,由于具备“行政犯”的属性,在行政机关做出违法性认定后的刑事阶段,情节之辩就显得尤其必要。
结语
证券市场本就是一个“逐利场”,这种特性使得它很容易被某些人用作非法牟利的工具,导致相关违法犯罪活动频繁发生。这些违法犯罪活动往往隐蔽性强、涉及专业知识深、侦查调查难度大,促使国家不断制定更为严格的法规以应对。证券、期货市场发展的脚步不会停歇,国家打击证券犯罪的力度也会随之加大,在这种趋势下,证券领域的刑事风险对企业而言,就如同悬挂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可能落下。作为资本市场的主角,上市公司及高管、关联人员等作为内幕信息获取的优势主体,应当在企业经营和自身履职过程中严格规范行为,加强合规治理,提升内控培训,强化行政法律边界及刑事法律红线,以保障企业在资本市场的行稳致远、扬帆远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