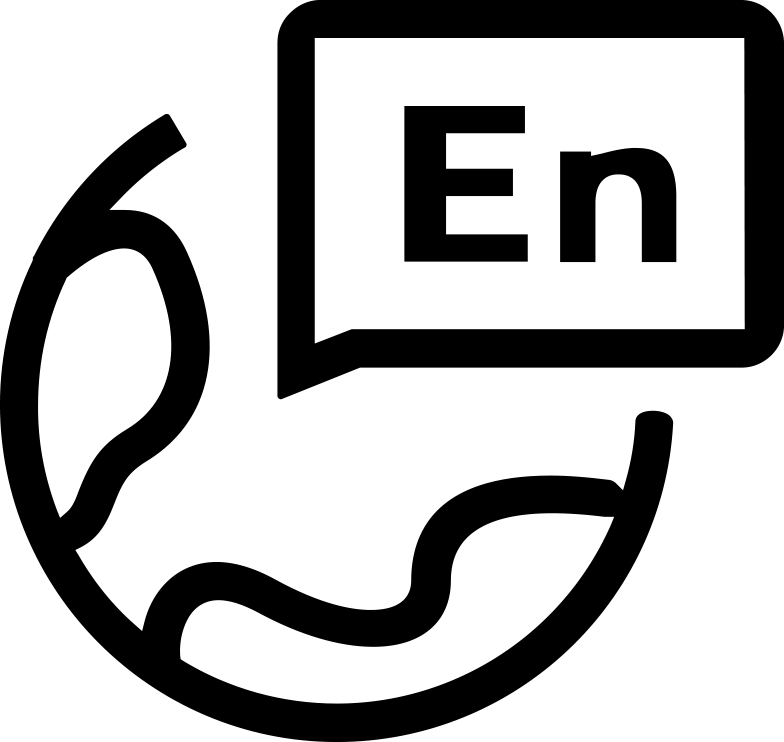我一直以为,正义的实现,不仅靠看得见的大动作,还有赖对具体问题的解决,对细节的落实。这里就“八孩母”案简单谈两个具体问题,也是拐卖类案件中的常见问题:监护及追诉时效,前者事关对弱者的切实保护,后者关乎对侵害行为的合法评价。
就此案来看,能够为杨某提供帮助的有几方力量:一方来自社会,主要是网络上有良知、愿发声的人,有的还曾到现场提供帮助,现在已经很难了。另一方是权力部门,正全力查办案件,回应社会关注,当然,还要考虑如何维护稳定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态。还有一方,就是这位妇女的亲属(以及所在村子里的宗族),事件曝光后,其亲属只流露出两个诉求:她的长子不希望外界干扰,他的丈夫不断要钱(现在没有机会了)而杨某本人,已得到初步的救治、看护。
如杨某这一类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属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即使经过治疗有所好转,大概率还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她不仅需要生存和健康保障,还需要得到全面的权益维护,包括对其个人财物、私人用品的保管,制订今后避免遭受侵害的方案,提出相关的诉求(赔偿等)等等,这些都是监护人的职责。她应该获得一位合格的、具有明确法律地位的监护人。
按照法定监护人的顺序,第一位顺序是“配偶”,就是她的丈夫董某,作为涉嫌侵害她的犯罪嫌疑人,应撤销其监护人资格。第二顺序为“父母、子女”,从已发布的信息看,其父母早亡多年,八个子女多是未成年人,其长子为成年人,似乎缺乏相应的监护能力。第三位顺序监护人为“其他亲属”,从杨某多年的境遇看,丈夫董某一方的亲属不合适,据报,已找到的杨某亲属远在外地,失联几十年,在客观条件和个人意愿方面,恐难履行监护职责。按法律规定,第四顺序监护人由有监护意愿的个人或者组织担任,目前看很难选择,而且法律规定,要经过当地居委会、村委会或者民政部门的同意。
那么有无其他救济途径?《民法典》还设有公职监护人制度,规定在监护人缺位的情况下,监护人由民政部门担任,也可以由具备履行监护职责条件的被监护人住所的居委会、村委会担任。现在政府有关部门在履行一定的临时监护职责,看来如无合适的人选,未来只能由当地民政部、村委会担任公职监护人了。
目前关于杨某的子女、家中老人已有监护的方案,杨某在健康、安全上获得一定保障,但如何让保障具有长期性、稳定性,她所遭受的巨大损失能否获得赔偿,其人格尊严、自由如何获得终身维护,怎样避免不法侵害,获得专业人士的帮助,除依靠政府、公众,还有赖于有能力、有担当的个人或相应的社会组织到位,充分行使监护权,这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就侵害行为看,很多观点把解决的入手点放在加重刑罚上,这多出于犯罪预防的考虑,对于尚未立案、尚未办结的拐卖类案件,更需要从执法角度解决,当然,执法不单是法律问题。拐卖类案件普遍取证困难,在执法中如何做到避免干预,全力查明案情,对涉嫌行为调查到何时、何地、何人,是否考虑回避(包括整体回避),在审查中如何确定嫌疑人范围,选取罪名,避免漏罪等等,远比立法修改要难。又如对追诉时效的审查,是拐卖类案件执法的一个关键环节,不少犯罪嫌疑人因追诉时效已过未被刑事追责。
对看似已过追诉时效的行为,不宜简单放弃,应考虑追诉时效中断的各种情形。以本案为例,官方通报显示,目前对董某选择的立案涉嫌罪名为非法拘禁罪,另两位嫌疑人的涉嫌罪名是拐卖妇女罪。按通报介绍,杨某被带到江苏是在1986年,这有可能是她被拐卖的最早时间,他被董某带走的具体时间通报里没有明确,有关报道称,杨、董二人的长子有二十三岁,表明她被董某带走的时间应在2000年之前的两三年。如果董某确有收买被拐卖妇女行为,其涉嫌行为发生在二十几年前,公案机关从未就此立案,也无人控告,不存在追诉时效延长的情形。
杨某是被董某买走,还是“捡”来的,尚在核实,如杨某当时已患有精神障碍,没有相应的辨别、自制和自卫能力,那么无论是“买”、还是“捡”,董某将其带回、长期限制其人身自由,就涉嫌构成非法拘禁罪,非法拘禁为持续状态,杨某依法脱离被拘禁状态之日,才是该罪追诉时效起算日。因非法拘禁行为发生在收买被拐卖妇女行为的追诉期限内,那么收买被拐卖妇女罪此前的时效期间符合中断条件,应重新计算。董某的涉嫌行为刚被以非法拘禁立案,所以,收买被拐卖妇女行为的追诉期限还未到期。
至于类似本案中涉嫌强奸的行为,现场证据已灭失,如有亲子鉴定结果及孩子年龄证明,可以确定行为发生的时间,由此不难对追诉时效作出判断。对于超过追诉时效的涉嫌强奸行为,要考虑前后涉嫌犯罪行为间可能存在的连续、牵连关系来判断。更大的难点在于对被害妇女患有精神障碍疾病的调查,需查证其发病时间,如确认发生性行为时妇女为精神病人,推定其不具有性的自我决定权,未征得女性同意,罪名即成立。
对拐卖类案件中涉嫌构成故意伤害罪、虐待罪行为,以及其他涉嫌行为,同样需要从行为关系、犯罪形态等角度来考虑追诉时效问题。
拐卖类案件从来不是单纯的法律问题,但就个案而言,还是要“用足法律”,希望在个案中不忘对弱者的关怀,保障其法定权利得以充分行使,对作恶者的追究、惩处,也有充分的法律依据,这才是具体的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