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证券公司、基金公司及其子公司、期货公司、保险公司纷纷推出资产管理计划之后,“银行版”资产管理计划在今年10月份也闪亮登场。首批11家试点银行发行完28只,总量为120亿理财直接融资工具后,新一批试点将在今年年底之前集中进行。与证券资管、保险资管等先行由监管部门推出监管法规不同,“银行版”资产管理计划的推出则尤抱琵琶半遮面,采取了先干起来再说的策略。之所以如此,监管机构有难言的苦衷。银行资管计划不仅饱受“通道”金融机构的质疑,而且面临远较其他资产管理计划更为复杂的法律问题。
一、银行与客户之间的关系定性——委托代理还是信托关系?
与《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将银行理财中的银行和客户之间界定为委托关系明显不同,银行资管计划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明显信托特征:第一,银行资管计划的受托人需要比理财计划的受托人承担更加严格的信托职责。传统的银行理财类似于银行存款,银行一般情况下向客户承诺一个预期收益率,募集资金后放入资金池,然后再去委托信托、券商、基金、保险等机构,与适合以上金融机构经营范围的项目进行对接就可以了。而银行资管计划则与信托计划一样先通过直接债权融资工具设计好投资项目,然后再通过银行资管计划去募集客户资金,需要比委托关系的受托人更要尽到“忠实和勤勉”的信托义务;第二,每一个银行资管计划的财产都是独立的。银行理财项目的资产端与资金端并非严格一一对应,资金和项目是混在一起的,尽管银监会8号文要求每一个理财计划分别建账、设专人管理,但难度很大。而每一个银行资管计划都是一个特殊目的实体(SPV),该计划管理的资产与原资产所有人的资产、银行资产、其他资产管理计划的资产彼此之间是独立的,这和信托法理是一致的;第三,银行资管计划的受托人与信托受托人一样取得的是财产管理服务报酬。如果受托人尽到了“善良管理人”的受托义务,即使该计划发生亏损,其后果要由委托人来承担。而传统的银行理财计划受托人取得的报酬的方式有些类似于银行信贷业务中的存贷款利差,银行承担了“刚性兑付”的隐性担保。因此,综上所述,银行资管计划中银行与客户之间的关系应该为信托关系。
如果将银行资管计划中银行与客户之间的关系定性为信托关系,将会与现行《商业银行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的“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经营业务”的规定相抵触。与银行资管计划同期推出的还有“债权直接融资工具”,该工具可能被定义为标准化产品,不受8号文非标产品占理财余额不能超过35%的限制。债权直接融资工具需要经过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的核查,需要增信机构增信,需要有债券评级,也要经过监管部门的审查,债权直接融资工具具有非常明显的债券特征。这与《商业银行法》第四十三条商业银行不能从事证券业务的规定相抵触,也是监管部门采取先干起来再说的策略的重要原因之一。解决以上冲突的方法有两种:第一,修改《商业银行法》,允许商业银行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经营业务。但该方法引发的法律风险非常大,会引起我国整个金融业发展格局的变化,短期内不具有可行性;第二,采取类似证券公司、基金公司建立二级子公司的做法,建立商业银行的资产管理公司。但问题是:无论银行顺利发行理财产品还是资管计划都是依托国家信用的隐性担保,一旦破除了刚性兑付,银行成立了具有法人资格的二级资产管理公司,投资者是否还像以往那样敢于购买资管计划或者理财产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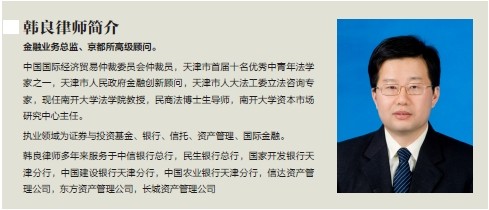
二、与监管机构的关系——单一监管还是多重监管?
按照监管部门的预期,银行资管计划应该是开放式的产品,与以往的理财产品有预期收益率的表现形式不同,更类似公募基金这种净值化产品,应该可以估值,可交易流转。目前的市场上,已经发行的银行理财资管产品包括工商银行推出的“中国工商银行超高净值客户专属多享优势系列产品—理财管理计划A款”,兴业银行的“兴业银行万利宝理财管理计划第一期第1款”,交通银行发售的“交通银行人民币理财管理计划2013年第一期”,以及浦发银行发行的“浦发银行月月享盈理财管理计划”,上述4款产品均为开放式、非保本浮动收益型,其申购赎回机制也与公募基金类似。如果将银行资管计划性质定位为公募基金,则银行资管计划应该符合《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规定,接受证监会的监管。
与银行理财计划的“类存款”运作方式不同,银行资管计划的资产端对应的是“债权直接融资工具”,虽然初期试点面向的是所谓的“合格投资者”发售,但从发行份额上来说,和以往的理财计划一样,应该远远超过了200份,属于我国证券法“公开发行”的范畴。前面说过,“债权直接融资工具”具有非常明显的债券特征,如果将其性质定义为我国证券法中的债券,毫无疑问,“债权直接融资工具”也要受中国证监会的监管。
此外,银行资产管理计划需在中国人民银行和财政部监管下的中债登登记托管,披露期限、净值、托管费用、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及报表报告等信息。按照正常监管职责,除了保监会之外,银行资产管理计划需要接受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的综合监管。尽管试点期间银行资管计划与债权直接融资工具回避了其公募基金与公开发行债券的资本市场属性,采取了监管套利的准生方式,但在我国金融业现行的“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下,注定其成长不会一帆风顺。
三、银行资管计划的产品投向——货币市场还是资本市场?
出于稳健经营的考虑,首批试点推出的银行资管计划的大部分资金,除了投向同业存款、货币基金、短融票据等高流动性货币市场资产外,还涉及资本市场的一些投资工具。如兴业银行的产品资金直接或间接投资于货币市场工具和银行间市场及证券交易所流通交易的债券、资产支持证券等有价证券、理财直接融资工具以及银监会认可的其他标准化金融投资工具。将银行资管计划的资金投向货币市场或者高流动性的债券市场无疑是正确的定位选择,也是其与券商资管计划、基金资管计划、保险资管计划的差异所在。但也有例外,工商银行的首批银行资管产品除投资于货币与债券市场外,还投资于一部分权益类资产,如新股及可分离债申购、可转换债申购、定向增发、股指期货、融资融券、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等。

很明显,如果不借助于通道业务,上述银行直接投资于资本市场的许多投资工具不仅违反了《商业银行法》四十三条规定的商业银行不能经营证券业务的禁止性规定,也与商业银行法规定的商业银行以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为经营原则相悖。因此,那种认为银行资管业务的推出将会完全“去通道化”的想法是站不住脚的,银行资管计划如果想做到合规,其投资到资本市场的许多投资工具还需要借助相关的“通道”。
四、银行资管计划能否成为信贷资产证券化的“SPV”
对银行资管计划的推出反响最大的金融机构当属信托公司,银行资管计划的推出不仅使一部分银信合作的“通道”业务受阻,更为重要的是使信托计划作为信贷资产证券化唯一法定的“SPV”地位岌岌可危,信托公司未来业务的空间被大大压缩了。信托公司的上述担心不无道理,这是因为:第一,作为银行资管计划的资产端,直接债权融资工具是将信贷资产等非标准资产转化为标准资产,其实就是一种证券化过程。尽管监管层认为直接融资工具是向企业发放新增债权性融资,而不是将银行的存量信贷资产打包成债券出售,但如果将基础资产换成银行存量资产是非常容易的事情,而这种转换就是典型的资产证券化;第二,《证券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第二条明确将证券公司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定义为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的特殊目的载体,将来会不会步券商的后尘,监管层将银行资管计划设为开展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的特殊目的载体呢?第三,即使监管层出于银行业与信托业同为其监管下同业兄弟的考虑,不会明确将银行资管计划定性为开展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的特殊目的载体,但银行业考虑到信贷资产证券化的风险、客户、资产都是自己的,面对信贷资产证券化复杂的审批程序和流程,还要转移相当一部分利润给作为受托人的信托公司,除非监管法规有强行规定,银行会利用其资管计划逐渐地将自己的信贷资产“证券化”。
银行利用其资管计划对自己的信贷资产进行“证券化”的操作很不规范,充满很大风险,第一,资产并没有实现真实出售,没有真正出表,风险仍然存留在银行自身,没有实现资产证券化的真正目的;第二,在信托关系不明确的情况下,银行自己同时充当发起人与受托人,容易引发道德风险;第三,由于银行资管计划没有相应的法律规范作为支撑,银行资管计划没有破产隔离功能,投资者将会面临极大的投资风险。
因此,应该出台监管法规对银行资管计划的投资范围做出严格的限定,将债权直接融资工具严格限定为向企业发放新增债权性融资,而不能购买银行存量的信贷资产,银行存量的信贷资产原则上只能通过实施标准的资产证券化方式出表。
银行资管计划与债权直接融资工具是“大资管时代”最具有震撼力的一次金融创新,其对“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金融体系与现行的金融监管法规带来的冲击都是空前的,体现了监管层推进利率市场化、金融服务现代化的决心。但其引发的法律问题是系统性的,非银监会一个部门所能解决的,需要“一行三会”进行多方协调,对银行法、信托法、证券法、保险法等金融法规进行系统的修订,打破部门利益的藩篱,使中国的金融行业走向真正风险可控的混业经营。



